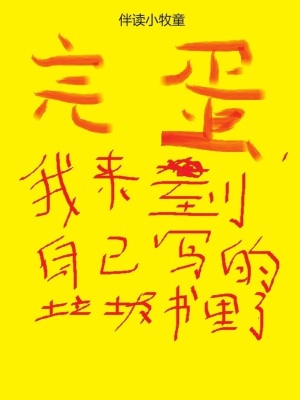暮色压城,细雨像一层极薄的纱,贴在瓦檐也贴在行人的肩背上。郡城里马蹄声散乱,青石板浸出黯光,街角有卖糖人的小槌“笃笃”敲着铜片,声细而急,像有谁心口也跟着敲。
破晓拢着衣襟,残刀斜背。他身形清瘦,步子不快,落在雨水里,不起半点花。他抬头时眼眸极亮,像潮夜里一线冷星。昨夜一宿功课,气息在胸腔里走了个小周,没能破关,却像在门槛上坐下了,伸手就摸得着门栓。
客栈门前,店伙计笑脸迎人,笑到眼尾都湿了霜似的。破晓在门边檐下抖掉袖口雨水,手掌收拢,指节骨骼分明,掌心老茧像细小的硬鳞。伙计端来一盏姜汤,热气扑面,驱去三分寒意。堂里坐了几人,衣裳笔挺的、腰间垂佩的,各自低声寒暄。靠窗有个青衣人侧坐,手指修长,端杯的姿势很稳,他看外头雨线,眼神却似在看人。那人嘴角轻挑,像是笑,又像在打量谁的脚印深浅。
破晓喝了一口姜汤,心下微暖,便起身上楼。踏到二层回廊,风从长窗钻进来,带着雨腥。走到拐角,他停了一停。楼角有淡淡药味,另有一股子铁锈气,极轻,像针尖挑破的血。那味道往里三步又折出去,落在对面尽头的一扇门前。门缝底下有水痕,不是雨,是鞋底带进去的。
他没有看门,只低低咳了一声,像不经意。他脚步再落,轻到听不出重量,绕过回廊,恰在楼梯口停住。下方有人慢慢上来,脚步沉重,踏实,像练过腿,稍一用力,木梯就会吱呀作响。上来的是个高个子,黑袍,帽檐极低,只露出半截下颌,胡渣剌手。他左臂袖口微鼓,藏了东西。后头又一人,精瘦,腰很细,眼神尖,像两枚细钉。两人登楼时不抬头,直到与破晓错身三尺,才一起停住。
黑袍人用一种与体型不相衬的低声笑,说:“兄弟,这楼里风大,别着凉。”精瘦的抬了一下下巴,眼神掠过破晓背后的刀。破晓看他们一眼,眸光淡,像看一双旧靴。他侧身让出半步,语气平平:“风确实大,小心受凉。”
两人侧过去,步子却慢。黑袍人的左袖轻轻鼓动一下,像水下鱼尾一甩,袖里寒光没出,他的肩却有一丝前探。破晓心里知道,前探不是试探,是先声。他右手落在刀背布带上,拇指顺着粗糙的麻纹往前推。那一下极轻,像把心里一盏灯推亮了半分。风从他耳畔穿过,带起门外雨丝簌簌地响,像有人翻书。
精瘦的忽然回身,靴底斜擦地板,腰间短匕闪出一寸。那去势不在前胸,反落在喉下,手腕带了个逆折,像蛇吐信。黑袍人在侧同时一靠,左袖里短矛“嗒”的一声弹出半截矛锋,直奔肋下空门。他们眼里没有杀气,只有办事的冷。
破晓没退。他掌心按过刀脊,残刀在肩上一滚,刀鞘撞护手发出极细的一声“磕”,像幼时母亲唤他名字前轻轻清喉。下一息,刀身出鞘半指,露出一道寒意,落在精瘦匕首上,轻轻一拨,像拨开草尖的露,毫不花俏,匕首便斜歪去了。他左脚落步,鞋跟压住木板缝,一寸不让。黑袍矛锋递至肋下,他沉腰,肋骨一收,肌肉挤出一道硬坎,矛锋擦着衣摆过,割出一痕,未进肉。
楼里烛火被风摇得一摇一摆,影子在墙上晃。精瘦的愣了一瞬,觉得手里的匕首像咬在了一块冰铁上,齿根酸。他换腕再刺,匕光跳出,如一尾银鱼翻水。破晓刀势并不快,只抬腕,刀身轻轻一震,夹住匕背。两柄兵器在空中贴了一贴,发出极短的一声脆响。精瘦的手虎口发麻,心里咒一句娘,脸却更冷。他知道这少年力道不大,架得住,是骨头里有股子韧劲,像山里雪松。
黑袍人不看同伴,手腕猛翻,矛锋回扎,招里带半分军中味,拳目是杀伤。他身上的气息收得极紧,像个沉水石。他盯住破晓腰眼,知道那是力气最难顾到的所在。破晓眼里反倒有一丝笑。他脚下踩了个极小的方位,右脚外摆三分,左脚斜跨半寸,像把一扇门轻轻掩上。黑袍矛锋扎来时,正好被门缝“卡”住了路,矛尖开不出花,他腰间刀背顺着矛杆一刷,露出一寸刀锋,贴着木杆向上一挑,黑袍人手腕“咯噔”一下,虎口刺痛,矛没丢,人却微抖。
那一抖里,破晓心口忽然“砰”地重重一响,像有人在胸膛里敲门。他耳边雨线声忽然稠了,烛芯噼啪声也稠了,楼底的姜汤翻泡声一颗颗地冒。所有声音都被他听见,清清楚楚。他知道,这是关口到了。小周天里那股气旋推着他,像把门栓往里一按,半寸再半寸,非要按开不可。
“现在不破,待何时。”他在心里说了一句,没人听见,连他自己都没出声。他的肩往前一送,像一匹饿狼起身去咬雪。刀身不再只露寸许,寒光又多了一分,雨味在舌根泛起来。精瘦的眼角抽了一抽,他看见那把破刀像雪里忽然伸出的霜枝,不华丽,冷硬。他想退,脚却被对方踏住了影子——并不是踏住脚,是气机先一步把他的路堵死了。
黑袍人低吼一声,矛杆横扫,半圆。这一下有力道也有杀心,若是普通人,胸肋要断几根。破晓不硬接,他肩背一塌,像一张弓弦松了又绷起,刀背被他当盾,斜挡过去,矛杆擦着刀背飞开,撞在廊柱上,发出一声闷响,柱上漆裂出一道细缝。黑袍人心下一沉,他知道眼前少年不是几招能拿下的货。他在江湖里做事,最怕碰上这种骨头——不吵不闹,手上干净。
“谁让你们上楼的?”楼下传来一声懒懒的问话,像谁含着笑骂人,玩世不恭里有一丝真寒。说话的人还未上来,气息先到了,像春水里一缕暗潮。黑袍人眼角一挑,余光里掠过一抹青色衣摆,心里骂声“晦气”。他不再恋战,矛锋一沉,收势,脚下连错三步,退得极干脆。精瘦的身子很轻,像把钉子从木里拔出来,后撤时连袖口都没飘,匕首却留在了原地——刀背刚才那一下,卡住了匕刃,往回抽时,匕柄断了。
破晓没追。他胸口那股气旋还在推,他怕一追,心口要炸开。他站着,背脊挺得直,像风里一杆旗。青衣人上楼时,笑得细,眼睛却凉,像刚从案牍里走出的文士。他把目光放在匕首折断的刃口上,轻轻“啧”了一声:“出手这般稳当,像哪家的老将教的。”
破晓收刀入鞘,刀入鞘时的那一声轻响,让他的心跟着落定半分。他拱手,语调平淡:“误闯贵人清静了。”
青衣人摇头,指尖在栏上点了点,像落雨一点点地点在江面。他道:“贵不贵,看谁来认。我只认好看不好看的事。你这把刀,不好看,太老,像边地回来的人,没学过一句漂亮话,偏要说理。”他笑起来,眼尾弯,像一柄折扇合上又开,“但我喜欢。”
他话里三分戏,七分试探。破晓不接,只微微颌首。他心里正忙,所有注意力都在胸腔里那团气上。那气此时像一条鱼,顶着水门,要冲过去。若错过,怕是又要耗上一阵。他深吸一口,只到胸,不到腹,再轻吐半寸,气从喉后绕过舌根,落入脐下。他身体微微一酥,眼前雨丝忽地被拉长了,城里远处的钟声从雾里传来,像敲在耳骨上。他听见自己心跳,像战鼓三声一落:咚,咚,咚。
青衣人斜眼看他,“小兄弟,你如今站在门槛上,脚要踏过,最好有人把门替你扶一扶。”他说着,侧身让出半步,回廊里风从他袖口掠过,带着墨香。破晓眼里闪过一丝讶色。他知道这句话不是闲话,是句好言。他低声道谢,不再多言。那青衣人嗯了一声,像把一滴酒含在嘴里,没咽下去,也不吐出来,挂在舌尖,叫人猜他喜怒。
楼下忽有店伙计喊:“客官,姜汤要续吗——”声音一下冲散了廊上细细的绷紧。破晓心头那条鱼正好顶过水门,一口气长出一寸。他不动声色,手背却出了层细汗。凝气不成,便是坎。此刻半步过去,像把脚从泥里拔出来,连着腿都沉。他站着,将要再走半步,忽听廊下街面上有马铃“当啷”一声,接着是马鼻沉哼。雨稍小了些,檐下人影一晃,进来三人,衣冠华整,腰佩玉,眉眼里生着骄矜。他们一进门,先寒暄,再抖袖摆摆样子。店小二赶紧迎上,弯腰如弓。
青衣人看去,眼里笑意更浅。他低声道:“庙里的人来了,江上也有几条船要靠岸。你可别在这门槛上坐太久,座位会被人拿走。”他向后退一步,微微作揖,像友人招手,也像在棋盘边让子:“楼底见。”
他走了,背影干净。破晓看他的背脊,觉得像一支笔,笔背里藏着风。回廊尽头那扇门忽然“吱呀”开了一线,有人站在门缝里,目光漠然,又似带笑。只看了破晓一眼,就合上门,没声息。那一眼像一枚冷钉,钉在他后心。他不追问是谁,只把刀带束紧,慢慢把气再往下送半分,像把一盏灯罩再压低一点,只让光透在桌面,不照亮天花。
他下楼时,楼外雨已成丝。堂里三位衣冠客正占了靠窗大桌,旁若无人地谈笑。左首那位指节戴着鸡血玉,指尖轻叩桌面,叩出个稳字。他们说的是郡城征粮,话头里有“配额”“盐引”“弩库”,每一个字都沾着百姓锅里的水汽,又都带火。破晓坐在角落,点了碗面,不抬眼,只听。他听他们把某个姓氏放在舌尖上反复打磨,又把某个门派的名号藏在袖底不露。他知道,这就是城里的雨,比天上的那场更细,也更冷。
面上桌,热气腾。他夹了一筷子,面很筋,汤里有姜味。他忽然想起父亲在家时,夜里常给他下面,面煮得略硬,汤里下两片葱白。父亲不说话,只把碗往他面前一推,就去看门口的风。母亲会从炉边递来一张饼,边角焦,留给自己吃,把中间鼓的那块掰给孩子。那时屋里灯小,屋外风大。如今灯仍小,风也大,人却不在。
他把那口面咽下去,胸口有火,火上覆着雪。青衣人从堂外折回,抬手在他桌沿指背轻敲两下,像敲琴。破晓抬眼,对上那人笑:“楼底见。”青衣人道:“嗯,见过了。”他视线一压,落到窗外,“还有人要见你。你这些日子敛得够久,今日不躲了。”
说这话时,门外风一阵猛,门帘扬起,露出街上那匹黑马一双眼。马鼻白气喷了两团,像两个小雾团。随马进来一人,灰袍,袖口干净,眉宇淡,眼睛却极深,像井里水。店里人都静了静,手上的筷子慢了半拍。
破晓微微转身,起立。他不握刀,手离刀一寸。他知这人是谁——昨夜回廊的压气如山,便是他。灰袍人看也不看堂里其余人,径直走到他桌前,坐下,手掌按在桌面,指尖敲了敲,三下,不轻不重:“吃。”
破晓应一声,坐下。青衣人笑着替两人添茶,茶色清,香浅。灰袍人抬眼,目光落在破晓的喉结上一瞬,便移开,“你胸口那口气,别急着逼到底,先带一小圈,再合。”
破晓“嗯”了一声,照做。气机果然柔了半分,像一匹马鬃被顺了。灰袍人又道:“你杀人时心不乱,这是好。心不乱,刀就不乱。但你心太直,直到容易被人看见。直要有弯,弯里还藏直。”他说话慢,像在说天色。
青衣人笑意加深,“前辈这一口子,像在庙里敲木鱼。”他看破晓,“听进去几分,便走得远几分。今夜城里要落一场不小的棋,你这碗面,吃完就上桌。”
破晓放下筷子,抬眼看两人。他很少说长句子,此时却开了口:“我只怕一个字——欠。”他顿了顿,“欠人情,欠性命。还不起,刀会重。”
灰袍人看他片刻,忽笑了笑,那笑在他脸上很轻,“那便把刀磨更利些。重,也能砍下去。”他目光掠过窗外雨帘,雨像老旧绸子被风扯了一把,“有人要借你名,有人要借你命。你若肯坐在棋盘上,他们便各有算盘。你若不肯坐……”他抬手,虚按,“也坐了。”
话到这,堂里那三位衣冠客忽然停了话头,最中间那位把手里鸡血玉转了一圈,抬眼:“两位可是为郡务出谋的高士?巧得很,今日也是来谈‘借’字的。”他瞥了破晓一眼,笑容薄,“这位小哥,手上有血,背上有霜,倒像是个合用的刀柄。”
破晓把茶盏轻轻放下。盏底碰桌的声音很轻,像雨滴落在檐角。他眼神沉静,指背搭在桌沿,虎口处那一层薄茧在烛火下像一圈白霜。他道:“刀柄合不合用,要看谁握。握久了,手会起泡,刀也会嫌。”
青衣人失笑,袖下折扇轻轻一合一张。灰袍人没笑,眼里却像落了一粒暖灰。他把身子往椅背一靠,像山往后退了半寸,“去。”
破晓起身。气机在胸腔再走一圈,像春雷窜过山谷,没炸,只滚。门口风把门帘吹起,他跨过去,雨落在他眉尖。他不举手去抹,任由那点凉沁入眼角。街面上行人稀,远处巷口有一抹影子,立着,不动,像一块碑。他抬脚,向那碑走去。背后,客栈堂里烛火摇,他听见青衣人低声一句:“这孩子,心上有雪。”灰袍人回:“雪在,就不怕火。”
雨更细了些,城也更冷。他把手落在刀柄上,像把话落在心里:此去,过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