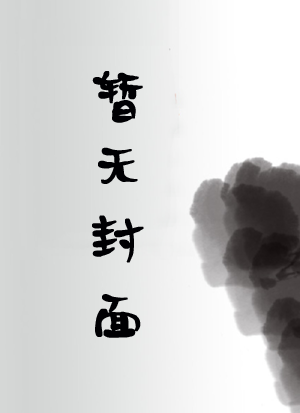又在茅屋苦修数日,沈砚望着窗外飘落的枯叶,心中对林晚意的牵挂越发浓烈。他整理好行囊,再次跪在聂涛面前:“师父,弟子有一事恳请应允。”
聂涛见他神色郑重,早已猜到几分,摆手道:“有话直说。”
沈砚叩首道:“请恕徒儿不孝,实在放心不下故友的生死。一月假期将至,徒儿想下山继续寻访她们的下落。”
聂涛闻言非但不恼,反而朗声大笑:“你也是重情义之人,这般心性,为师甚是欣慰。”他起身走到沈砚身边,递过一把通体乌黑的长刀,“这柄‘裂风’你带着防身。”
他望着昆邪山深处,忽然道:“山巅有座青云观,地势险峻,寻常人根本上不去。你若寻不到线索,可去那里寻访一番,或许能解了你的疑惑。”沈砚接过长刀,再次叩谢师恩,转身踏入了茫茫山林。
昆邪山巅隐在缥缈的云雾中,青云观的飞檐似从云端探出,若隐若现。通往观门的路根本称不上路,尽是陡峭的岩壁与松动的碎石,寻常人莫说攀登,连仰望都觉眩晕。
沈砚握紧腰间的裂风刀,丹田内真气流转不息。他踩着混沌心法与通天玄功融合的步法,如猿猴般在峭壁间腾跃,指尖抠住岩缝借力,脚掌踏碎松动的石块,汗水顺着脸颊滑落,瞬间被山风蒸发。翻过最后一道垂直的崖壁时,他手臂的肌肉因过度用力而微微颤抖,却终究抓住了崖顶的杂草,翻身落在平整的台地上。
眼前豁然开朗,一座古朴的道观静静矗立在云雾中,青砖灰瓦上覆着薄薄的青苔,门前的铜鹤香炉正飘着袅袅青烟。一名身着素色道袍的中年道姑已立在观门阶前,发髻梳得一丝不苟,面容沉静如水。 “施主劳累了。”道姑微微颔首,声音清越如泉,“贫道静仪,有礼了。” 沈砚连忙收敛起一身风尘,拱手行礼:“打扰师太清修,在下沈砚实在唐突。”他望着静仪淡然的目光,坦诚道,“只因担忧故人安危,听闻山巅道观或许有线索,才敢冒死攀登造次,还望师太见谅。” 静仪侧身让开道路,语气依旧平淡:“施主有心了。”她转身向观内走去,青布鞋踏在石板上悄无声息,“世间万物,祸福自有天定,强求不得,也无须庸人自扰。” 沈砚闻言愕然,脚步顿在原地。他历经艰险攀上这云端道观,原以为能得到些许故人的音讯,却只换来这般虚无缥缈的回答。难道晚意她们真的……他不敢再想下去,指尖下意识又攥紧了怀中的香囊。 静仪似是看穿了他的心思,在丹房前停下脚步,转过身来。阳光透过云雾洒在她素净的脸上,竟有种不似凡尘的温润:“施主不必介怀,贫道并非不愿相告。”她望着远处翻涌的云海,“只是有些事,知道了反而徒增烦恼。” 沈砚急切地上前一步:“师太,哪怕只有一丝希望,我也想知道她们是否安好!” 静仪轻轻摇头,目光落在他腰间的裂风刀上,又扫过他周身隐约流转的真气,忽然话锋一转:“施主可知,你身负混沌道体,又习得神刀门心法,与仙家早已结下缘分?” 沈砚一愣,不知她为何提及此事:“师太的意思是……” “尘缘未了,仙途难开。”静仪的声音带着一丝缥缈,“你如今身陷俗世纠葛,于修行无益。若想窥得大道,须当了了尘缘,方能心无挂碍。”她抬手指向丹房内的香炉,“这观中香火千年未断,能照见过往未来,施主若信得过贫道,可在此静心打坐三日,或许自会有答案。” 沈砚望着静仪平静无波的眼睛,又回头望了望山下云雾缭绕的深渊。一边是牵肠挂肚的故人下落,一边是关乎修行的尘缘点拨,他站在这云端道观的丹房前,忽然陷入了两难的抉择。风从观外吹来,带着山间的清冽气息,仿佛在催促他做出决定。 沈砚望着静仪淡然的神色,心中虽仍记挂着林晚意的下落,却也明白此刻急切无用。他深吸一口气,拱手道:“师太所言极是,既来之则安之,在下便在此叨扰三日。” 静仪微微颔首,转身引着他穿过道观的回廊。青石铺就的路面干净无尘,两侧的松柏修剪得整整齐齐,偶尔有几只灰鸽落在屋檐上,见了人也不惊慌。穿过前殿,后院竟是一处雅致的小院,院中凿有一方石井,井边种着几株翠竹,风过叶响,格外清幽。 “这边请。”静仪推开一间素雅的静室木门。屋内陈设极简,只有一张木榻、一张蒲团和一张矮桌,墙上挂着一幅水墨山水图,角落里燃着一炉沉香,烟气袅袅上升,带着安神定气的功效。 “这三日你便在此静修,每日三餐自有小道送来,不必操心外事。”静仪将一盏清茶放在矮桌上,“香炉里燃的是凝神香,有助你静心。若能摒除杂念,或许能在静定中窥见些什么。” 沈砚谢过静仪,待她离开后,便在蒲团上盘膝坐下。他本想运转通天玄功,可刚凝神静气,脑海中便闪过宛城的荒寂、秦府的残垣,还有林晚意绣在香囊上的杏花。那些画面挥之不去,让他心绪难平。 不知过了多久,沉香的气息渐渐侵入心脾,沈砚忽然想起聂涛的教诲,试着用混沌心法引导呼吸。随着内息缓缓流转,那些纷乱的思绪竟慢慢沉淀下来,眼前仿佛浮现出云雾缭绕的山巅,又隐约看到一抹杏色的身影在林间穿行。 静室格外安静,只有沉香的烟气在晨光中缓缓浮动。沈砚起初难以入定,脑海中总闪过晚意的笑脸、边关的尸骨、聂涛的刀谱,种种画面交织翻涌,让他心乱如麻。他强迫自己闭上眼,依混沌心法引导呼吸,可真气刚运转片刻,便因心绪不宁而滞涩难行。 静仪送来的清茶放在桌角,茶汤渐渐凉透。沈砚望着袅袅升起的香烟,忽然想起聂涛练刀时的专注——刀在手中,便只有刀;气在体内,便只随气行。他重新调整坐姿,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呼吸上,感受气息从鼻腔吸入,沉入丹田,再缓缓呼出。 如此反复数次,纷乱的思绪竟如退潮般渐渐平息。当夕阳透过窗棂照在蒲团上时,沈砚忽然觉得身心轻盈了许多,体内真气流转顺畅无比,周遭的声响也变得格外清晰——能听见院外竹影婆娑,能闻见远处香炉的余韵。 第二日清晨,沈砚在鸟鸣中睁眼,昨日静心的澄明仍在心底。他盘膝坐定,不再刻意控制呼吸,任由混沌真气自然流转。 随着心神越发宁静,奇妙的变化悄然发生。他能“看”到窗外竹枝的轻颤,能“听”到石阶上露珠滚落的微响,甚至能感应到远处山林中野兽的呼吸。真气在体内游走时,仿佛与周遭的草木风声产生了共鸣。 当静仪送来斋饭时,沈砚竟提前察觉到她的脚步声。他睁开眼,心中满是震撼——原来静心之后,身外万物的气息竟能如此清晰地感应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