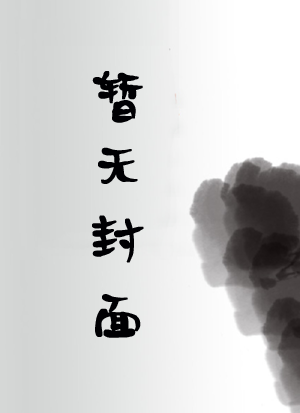第三日午后,静仪轻叩静室之门。沈砚起身相迎时,只觉周身气息与清晨又有不同,仿佛与这山间云雾都有了微妙的联系。
“看来施主已有收获。”静仪望着他,眼中闪过一丝赞许,“今日与你论道,或许能解你心中疑惑。”她在蒲团上坐下,指尖轻叩桌面,“天地万物皆分阴阳,阴阳相济而生五行,五行轮转而成世间百态。”
沈砚凝神倾听,只听静仪继续道:“刀有刚猛,亦有柔转,正如阳中有阴;气有流转,亦有凝聚,恰如阴中含阳。你练裂风刀重杀伐,修混沌心法重圆融,若能悟透阴阳相生之理,武技自会更上一层。”
她指尖划过桌面,留下淡淡的痕迹:“五行相生相克,正如人事聚散离合。你牵挂的故人,若命中有此一劫,强求不得;若缘分未尽,自会在合适之时重逢。”
沈砚闻言如遭雷击,脑中轰然作响。过往练刀时的滞涩、心法中的瓶颈,此刻竟豁然开朗。他望着静仪平静的面容,忽然明白——所谓尘缘,并非要刻意割舍,而是要在牵挂中保持清明;所谓修行,也并非远离俗世,而是要在百态中悟透根本。这一刻,他心中的焦灼渐渐散去,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澄明。
沈砚在静室中枯坐一夜,静仪的论道之言在脑海中反复回荡,可心中却生出新的迷茫。他望着窗外渐亮的天色,喃喃自语:“人生究竟有何意义?”想起戍边的岁月,想起那些战死的袍泽,想起孙大力他们决绝的背影,他越发困惑——自己守着那座雁门关,究竟是对是错?是护了家国,还是误了性命?
第四日凌晨,晨钟在青云观上空响起,清越的钟声穿透云雾,直入人心。沈砚正心乱如麻,静仪已推门而入,手中托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粥。
“施主一夜未眠?”静仪将米粥放在桌上,目光温和,“心中可有困惑?”
沈砚抬头苦笑:“师太,弟子参不透人生的意义,也分不清过往的对错。”
静仪指了指窗外初升的朝阳:“朝阳东起西落,从不论意义,却温暖万物;草木春生秋枯,从不论对错,却滋养大地。”她舀起一勺米粥,“你戍边是护百姓安宁,寻友是守心中情义,只要所作所为问心无愧,便是意义所在。”
钟声再次响起,沈砚望着晨光中的远山,忽然心头一震。是啊,人生本无定法,对错自在心间。他起身深深一揖:“多谢师太点化,弟子明白了!”
沈砚对着殿门深深一揖,转身告辞。来时那条需攀援藤蔓的峭壁小径并未再走,他循着山侧一条蜿蜒石阶缓缓而下。石阶被经年落叶覆盖,踩上去簌簌作响,偶有阳光透过层叠枝叶,在路面投下斑驳光点。
行至山腰处,林间风势渐起,卷着草木清气拂过面颊。他下意识驻足回头,却见方才还清晰可见的殿阁已隐入茫茫云雾之中。原本青灰色的檐角、朱红色的梁柱,此刻都被流动的白霭吞没,只剩一片朦胧的轮廓在云层中若隐若现,仿佛海市蜃楼般虚幻。
山风更盛,云雾翻涌间,连那点轮廓也渐渐淡去。沈砚望着空濛的山巅,指尖还残留着殿中檀香的余温,耳畔却已只剩林间鸟鸣与风声。他轻轻叹了口气,转身继续沿山路向下,身后的仙境便彻底隐没在群山之中。
沈砚掐指算来,一月假期已近尾声,尚余五日闲暇,正好启程返程。他行至山脚客栈,取回先前寄存的快马,解了缰绳翻身上鞍。马蹄轻踏山路,向着雁门关方向缓缓而行,不急不躁。风拂过耳畔,带着山间草木清气,一路蹄声伴着归程心绪。
行出百余里,前方渐显人烟,嵊县城墙在日光下隐约可见。相较山间的清幽,此处显然繁华得多,街道上车马往来,叫卖声此起彼伏,一派热闹景象。此时日已近午,暑气渐升,沈砚勒住缰绳,在街角寻了家挂着“迎客楼”幌子的酒店。
他将战马交给迎上来的店小二,特意叮嘱多加些精料好生照看,随后拾级上了二楼。选了个临窗的雅座坐下,窗外便是熙攘的街市。他唤来店家,点了盘酱鸭、一碟时鲜青菜,又要了壶本地米酒温着。
不多时酒菜上桌,琥珀色的酒液在杯中晃出涟漪,酱香混着酒香漫开。沈砚执杯凭窗,一边小口啜饮,一边看着楼下行人往来,听着邻桌的说笑声,旅途的疲惫在这烟火气中渐渐消散,只觉身心都松快了几分。
邻窗的交谈声断断续续飘来,恰好落入沈砚耳中。一位身着长衫的中年文士正端着酒杯叹气,声音里满是牢骚:“年关岁末本就该安稳度日,偏偏又下了征兵文书,乡里到处敲锣吆喝,真是搞得鸡飞狗跳不得安宁。”说罢转向对面商人模样的圆脸汉子,“张老板这生意,想必也受了不少影响吧?”
那商人连忙摆手,脸上堆着笑应道:“王兄有心了!如今国难当头,北境不宁,咱们能在这城里苟活于世已是万幸,生意好坏又算得了什么。”他话锋一转,看向席间最年轻的青衫男子,“倒是蔡兄弟吃着公家饭,在县衙当差,才是如今活得最滋润的。”
年青男子闻言挺直了腰板,意气风发地摆手:“张老板客气了!这几日被征兵的琐事缠得脚不沾地,哪谈得上滋润。明儿忙完了,正好去拜访下高府公子,过不了多久,人家该是高将军了!”
张老板脸上的笑容更甚,凑近了些问道:“你说的是高尚书家那位公子?听闻他自幼饱读诗书,怎么也去戍边了?这金枝玉叶去那苦寒之地,可吃得消?”三人的谈话渐渐转向对高公子从军的议论,沈砚执杯的手指微微一顿,目光望向窗外,若有所思地抿了口酒。
邻窗的王秀才眼中顿时燃起八卦之火,身子往前凑了凑:“蔡帮办这话在理!高尚书在朝中地位显赫,为官多年口碑素来不错,门生故吏遍布朝野。高公子这一去戍边,凭着高家的声望,定能召集一群世家子弟从军,说不定过两年就能当上雁门关主将,那可是手握重兵的要职!”
蔡帮办闻言却面色一凛,连忙抬手示意他压低声音,自己也凑近了些,声音压得极低:“王兄慎言!这种话私下说说便罢,不可外传。大家心里有数就行。”他端起茶杯抿了口,目光扫过四周才继续道,“你们有所不知,高尚书家庄客众多,暗中蓄养的武师更是不在少数,本就势力庞大。如今公子去戍边,倘若真要举事,凭着高家的号召力,自然是一呼百应。”
“举事”二字如惊雷般落入沈砚耳中,他握着酒杯的手猛地一顿,酒液险些晃出杯外。他不动声色地转回头,眼角余光却仍留意着邻桌。高尚书……原来这位看似清正的高官竟暗中积蓄力量至此?连县衙小吏都知晓其势力,看来此人确实不简单。沈砚心中警铃大作,面上却依旧平静,只将杯中残酒缓缓饮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