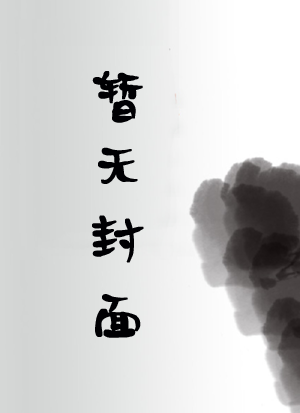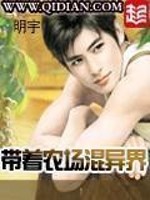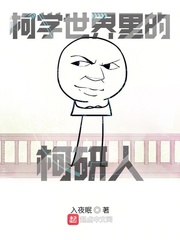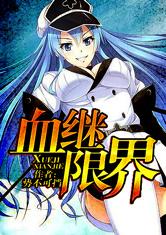第九章:焚书坑儒掩秘辛
第九章:焚书坑儒掩秘辛
骊山地宫渗水的阴湿气息,如同跗骨之蛆,尚未从咸阳宫巍峨的殿柱与冰冷的金砖地面彻底散去,另一股源于人心深处、更为肃杀酷烈的寒流,已伴随着关中秋日的肃杀之气,开始如瘟疫般席卷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市井坊间,关于龙脉震怒、天罚暴政的窃语,不再是暗流涌动,而是如同决堤的洪水,在酒肆、闾巷、田间地头奔腾咆哮。这些流言,与那些对严刑峻法、无休止徭役的怨愤,以及儒生博士们对郡县制、以吏为师的公开非议交织在一起,形成一股越来越汹涌的、质疑皇帝权威和帝国根本政策的暗潮,不断冲击着嬴政那日益刚愎自用、不容丝毫挑战的神经。
这一日,天空依旧阴沉。丞相李斯手持一卷写满各地密报的沉甸甸竹简,步履比往日更加沉重,几乎是一步一顿地走入庄严肃穆的章台宫。宫门外甲士林立,戟铳森然,空气中弥漫着无形的压力。李斯的面色凝重得如同此时的天气,眉宇间积压着风暴来临前浓得化不开的乌云,他知道,手中这卷竹简所承载的信息,足以在帝国掀起一场滔天巨浪。
“陛下,”李斯行至御阶之下,伏地行大礼,声音带着刻意压制却仍能听出的沉痛与紧迫,“臣李斯,有紧急要务奏报。”
嬴政正端坐在高高的御座之上,身披玄色龙纹深衣,面前堆积如山的竹简暂时被推开。他并未像往常一样立刻让李斯平身,只是用那双深陷却锐利如鹰隼的眼睛,冷冷地俯视着跪伏在地的丞相,仿佛在审视一件工具是否仍堪使用。殿内侍立的宦官、宫女皆屏息凝神,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讲。”良久,嬴政才吐出一个冰冷的字眼。
李斯深吸一口气,将竹简高举过头顶,语速加快:“陛下,三川、河东、颍川、泗水……乃至京畿内史,各郡守、监御史连日来急报如雪片!闾巷之间,非议朝政者日嚣尘上,已非私下窃语,几近公然谤讪!更有原齐、鲁、楚等地遗老,以及那些……那些终日以传承古礼自居的儒生博士,非但抨击郡县之制,诋毁陛下法令,更将骊山地宫渗水之事,引为攻讦之口实,妄言此乃……乃陛下德不配位,故天降灾异以示惩戒!”最后一句,他几乎是咬着牙说出来的,额角渗出细密的冷汗,深知这将如何猛烈地触怒御座上的君王。
出乎意料,嬴政并未立刻勃然作色。他那张因长期勤政和追求长生而略显灰暗的脸上,肌肉微微抽搐了一下,但更多的是一种极寒的平静。他的目光缓缓从李斯身上移开,投向殿外那片被秋雨洗刷后依旧阴郁的天空,手指无意识地、一下下地敲击着紫檀木御座的扶手,发出沉闷而规律的“笃、笃”声。这声音在寂静的大殿中回荡,比任何咆哮都更令人心悸,每一下都仿佛敲在殿内所有人的心脏上。
“德不配位……天降灾异……”嬴政低声重复着这两个词,声音平淡得没有一丝波澜,却蕴含着火山喷发前那种令人窒息的死寂。他扫灭六国,统一海内,自认功业超越三皇五帝,建立起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帝国,最根深蒂固的逆鳞,便是这等以古非今、假借天意质疑其统治合法性的言论!“朕横扫六合,奠定乾坤,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设郡县以废分封,此乃开天辟地之伟业,足以泽被万世!那些腐儒,鼠目寸光,终日只知抱守残缺,妄议朕之法度,其心可诛!如今竟敢借骊山之事,妖言惑众,动摇国本!”
他的声音逐渐拔高,冰冷的怒意如同千年玄冰打造的利剑,骤然出鞘,寒光四射,瞬间冻结了整个大殿的空气:“李斯!你是丞相,总领天下政务。对此等惑乱民心、动摇国本之猖獗之举,有何良策?朕要听的,是根除之法,而非隔靴搔痒!”
李斯感受到那如同实质的威压,心知决定帝国文化命运乃至无数人生死的时刻到了。他再次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抬起头,目光迎向嬴政那深不见底的眼眸,开始了早已在腹中反复推敲、酝酿成熟的陈词。他知道,必须一击必中,彻底说服皇帝。
“陛下!”李斯的声音陡然变得激昂起来,带着一种为国除奸的凛然之气,“臣尝闻,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其治,非其故意相反,乃时势变异使然!夏、商、周三代治法不同,并非后者故意要反其道而行之,而是因为时代变了,治理的方法也必须随之改变!今陛下创万世未有之功业,立千秋不易之法度,废分封而设郡县,此乃顺应天下一统之大势,岂是那些只知道诵《诗》《书》、言必称尧舜、墨守成规的愚儒所能理解?” 他观察到嬴政的眼神微微闪动,知道说中了皇帝的心思,便趁热打铁,语气愈发尖锐:“然纵观当下之患,其根源在于私学盛行!诸生不学习当今陛下颁布的英明法令,反而一味师从古法,以古非今,蛊惑黔首!丞相臣斯昧死以言:古者天下散乱,诸侯并立,故言语各异,学说纷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人皆以为自家所学最为高明,用以非难其上之所建立。此乃天下纷争之源也!” 李斯停顿片刻,让话语的份量沉淀下去,然后抛出了最核心的指控,语气变得痛心疾首:“今皇帝陛下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扫灭百家争鸣之乱象,此乃江山永固之基!然如今,私学之风复炽,诸生闻朝廷法令下,则各以其所学妄加议论,入朝则心非,出朝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此风若不加以严禁,则主上之威权必然降低于朝廷,朋党之势必形成于下面!禁之,则有利于国家安定;纵之,则后患无穷!臣恳请陛下,必须严禁此风!” 这一番长篇大论,引经据典,逻辑层层递进,将诸子百家(尤其是儒家)的私学传承和自由议论,直接定性为结党营私、威胁中央集权、导致天下混乱的毒瘤。最后“必须严禁”四字,斩钉截铁,不容置疑,提出了最极端也最符合法家思想的解决方案。 嬴政眼中寒光大盛,身体微微前倾。李斯的话,如同一把钥匙,精准地打开了他内心最深处的焦虑与意志。他追求的不止是疆土的统一,更是思想的绝对一统,是让四海之内只有一种声音——那就是他秦始皇的声音!任何杂音,都必须被彻底、干净、彻底地清除!百家争鸣的时代必须彻底终结! “如何禁法?”嬴政追问,语气中已带上了不容置疑的决断和一丝急不可耐,“朕要具体之策!” 李斯心知奏效,胸中块垒稍去,他毫不迟疑地、清晰而冷酷地抛出了那足以令天下文人胆寒、令文明蒙尘的石破天惊之策:“臣冒死恳请陛下颁行天下: 其一,命史官,将非秦国之史书,尤其是诸侯史记,悉数查缴焚毁,使后人无法以古非今,惑乱天下! 其二,除博士官因职守所需可收藏《诗》、《书》、百家语之外,天下敢有私藏上述书籍者,限期之内,必须将书籍全部送至郡守、郡尉衙门,集中统一烧毁! 其三,有敢偶语《诗》、《书》者,一经发现,弃市处死,以儆效尤! 其四,最重者,以古非今者,罪不容诛,处以族刑,满门抄斩! 其五,官吏见知而不举报者,与犯者同罪,绝不姑息! 其六,此令下达后,三十日为限,逾期不焚书者,黥面(脸上刺字),罚为城旦(筑城苦役)! 其七,天下书籍,唯有医药、卜筮、种树之类实用技艺之书,可以保留不禁。 其八,若欲求学,今后不必师从私学,应以官吏为师,学习国家法令即可!” 这便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焚书令”的完整雏形!它不仅是要从物理上消灭绝大部分历史典籍和诸子百家思想遗产,更要从根本上禁绝一切自由讨论的空间,实行严厉的连坐制度,用最残酷的刑罚来确保文化专制和思想禁锢的彻底执行。只保留那些对维持帝国运转和百姓基本生存有直接用途的实用技术书籍,并将教育权完全收归国家机器,培养只知法令、不懂其他的顺民。 残酷,但对于追求绝对掌控、杜绝一切不稳定因素的嬴政而言,却显得如此“高效”、“必要”甚至“一劳永逸”。 章台宫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铜漏的滴答声此刻显得异常刺耳。侍立的宦官宫女们个个面无人色,低头缩颈,恨不得将自己缩进地缝里。李斯跪伏在地,屏住呼吸,等待着最终的裁决,他能清晰地听到自己心脏狂跳的声音。 时间仿佛凝固了。嬴政的手指停止了敲击,他深邃的目光扫过殿下跪着的李斯,又似乎穿透了宫殿的墙壁,看到了帝国广袤的疆域和那些即将在烈火中化为灰烬的竹简帛书。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一种近乎神性的冷酷和决绝。 “准。” 一个冰冷的字眼,如同终审的判决,从嬴政口中吐出,没有丝毫犹豫,不带一丝感情。 “就依你所奏,即刻拟诏,颁行天下!朕要这四海之内,八荒之地,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思想!凡有违抗此令者,无论何人,杀无赦!朕倒要看看,是他们的脖子硬,还是朕的刀剑利!” “臣!领旨!”李斯心中那块巨大的石头轰然落地,他几乎是匍匐着深深叩首,额头触及冰冷的地面,眼底深处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混合着如释重负和权力欲望得逞的复杂神色。这场由骊山工程事故引发的政治风暴,终于被他成功地引导向了彻底铲除儒家等学派、确立法家思想绝对独尊的决定性方向。他知道,一场席卷整个帝国的文化浩劫,即将由他亲手拉开序幕。 然而,就在李斯以为大功告成,准备告退去紧急草拟诏书细节之时,一直如同幽魂般侍立在嬴政御座旁阴影中的中车府令赵高,微微动了动。他像一条滑腻的毒蛇,悄无声息地向前挪了半步,躬身,用一种谦卑到极致、几乎如同耳语却又清晰可闻的阴柔嗓音开口了: “陛下圣明,烛照万里。李丞相此策,高瞻远瞩,实乃廓清寰宇、永固江山社稷之万年基石。”他先是用谄媚到肉麻的语调定了性,随即话锋如同淬毒的匕首般,悄然转向,刺向了更隐秘、更阴险的方向,“然……奴婢愚钝,斗胆妄言,窃以为这流言蜚语之根源,除了那些摇唇鼓舌、徒逞口舌之快的儒生,或许……还有更贴近地面、更不易察觉的祸水源头,若不断其根,恐焚书之举,犹似扬汤止沸。” 嬴政刚刚做出重大决策,心神未定,闻言目光骤然转回,如同两道利箭射向赵高。李斯也是心中一凛,即将站起的身子又顿住了,警惕地看向这个深得帝心、心思难测的宦官。 赵高保持着极度谦卑的躬身姿态,头垂得更低,继续用他那特有的、带着阴柔磁性的危险语调说道:“陛下明鉴,骊山陵寝工程,汇聚四方役夫、六国刑徒,数以十万计,鱼龙混杂,人心回测。此次地宫渗水,死伤惨重,那些侥幸生还之人,亲眼目睹地底异状,亲身经历生死恐怖,心中之积怨恐惧,已然深种。若任由他们将所见所闻,添油加醋,散播于市井乡野……这些来自工程最底层、带着泥土和血腥气的‘亲眼见证’,恐怕比儒生们在书斋里的纸上空谈,更能蛊惑那些无知愚民,引发更大的恐慌和动荡啊。” 他略作停顿,让这番暗示的危险性充分渗透进寂静的空气,然后抛出了更致命、更直指嬴政内心隐忧的筹码:“况且,陛下,地宫工程深掘千尺,触及幽冥,难免会发掘出一些……年代久远、形制古怪、非同寻常之物。譬如,方士韩终先生此前曾隐约提及的那些……可能源自上古的‘遗存’。若这些物件,或其引发的种种难以解释的异象,被那些粗鄙不文、心怀怨怼的役夫歪曲解读,再经由某些包藏祸心之辈刻意传播放大,恐会衍生出更加荒诞离奇、甚至……直指陛下洪福齐天与万年吉壤安稳的恶毒谣言。此类谣言,若与儒生们的诽谤合流,其危害……奴婢不敢想象。届时,只怕单凭焚书之烈举,犹恐难以斩草除根,永绝后患。” 赵高此言,极其阴险狠辣,展现了他对人性阴暗面和政治权术的深刻理解。他巧妙地将打击面从抽象的“思想犯”(儒生)扩大到了具体的“潜在目击者”和“信息源”(工程役夫)。一方面,他暗示必须加强对骊山工程相关人员(尤其是事故幸存者)的严格控制,乃至……进行彻底的、物理上的清理,以绝后患;另一方面,他再次精准地强调了“上古遗存”的特殊性和极度敏感性,并将其与始皇最核心、最敏感的长生梦想和陵寝吉凶直接挂钩,暗示此类超越常人理解的“秘密”信息的发掘、掌控与解读,必须由绝对可靠、直接对皇帝负责的、超越常规官僚体系的特殊渠道来垄断——而这个渠道的最佳、也是最理想的掌控者,自然是他这个日夜伴随皇帝左右、深得信任的赵高本人。 嬴政的眉头深深锁起,形成了一个川字。赵高的话,像一根毒刺,精准地戳中了他内心最深处的隐忧。他追求长生不死,最忌讳的就是不祥之兆和不利的舆论,尤其是涉及他陵寝和长生之事。如果地底挖出的东西被那些愚民曲解成对他或他的万年吉壤不利的象征,甚至与“天谴”联系起来,那将是对他信念和权威的双重打击,后果不堪设想。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必须将任何可能的隐患扼杀在萌芽状态! “嗯……”嬴政沉吟片刻,眼中闪过冷酷决绝的光芒,他看向李斯,语气不容置疑:“李斯,焚书之事,由你全权督办,务求雷厉风行,迅疾如火,震慑天下!朕要看到咸阳城率先燃起焚书之火!至于骊山工程的数十万役夫,尤其是此次地宫渗水事故的幸存者……”他的话语在这里顿了顿,空气中弥漫开一股浓重的血腥味,仿佛无数人命已然悬于一线,“你要会同廷尉府、监御史以及骊山督造官员,立即进行严密甄别,加强管控!凡有散播谣言、形迹可疑、甚至仅仅是可能接触过地底异常之物者,立地处决,毋需审判,毋需宽宥!必要之时……” 嬴政的目光变得幽深而残酷,仿佛回到了当年决定长平之战降卒命运的时刻,“……可效法武安君旧事,以绝后患!朕不允许有任何污秽之言,玷污朕的吉壤,动摇帝国的根基!你,明白吗?” “武安君旧事”这五个字,如同寒冬惊雷,在李斯耳边炸响。那是武安君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卒的惨烈典故!陛下此言,分明是默许甚至鼓励对大量知情或可能知情的役夫进行大规模的血腥清洗!李斯瞬间感到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后背顷刻间被冷汗浸透。但他深知,此刻任何犹豫或劝谏都是徒劳且危险的。他强行压下心中的悸动,以头抢地,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臣……明白!陛下放心,臣定当会同有关衙署,妥善……处置,绝不使陛下为此等琐事忧心!定将一切隐患,扑灭于未燃之时!” 赵高则顺势进一步说道,语气更加谦卑,内容却更加深入核心:“陛下圣虑深远,明察秋毫。奴婢拜服。至于地宫深处所出之异物,及相关一切异状,关乎骊山地脉龙气、陛下万年吉壤之安稳,乃至国运之兴衰,干系实在重大,不容丝毫闪失。奴婢愚见,当设一专司,或指定绝对可靠之心腹,严加监控,所有发现,无论巨细、无论吉凶,皆需密封加印,直达天听,由陛下圣心独断。韩终先生虽精于丹道方术,然此事牵涉甚广,远超丹鼎之学的范畴,或需……更为缜密、周全、可靠的考量与处置,以免片言只语外泄,为奸佞小人所乘,酿成大祸。”他这是在委婉却坚定地建议,应建立一个超越韩终、直接由皇帝(或者说由他赵高)掌控的秘密情报与应急处置系统,将骊山最核心的秘密完全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下。 嬴政深深地看了赵高一眼,此次并未立刻表态,但眼神中的意味已然明了。他需要绝对的控制,尤其是关于长生和陵寝的秘密。“此事,朕自有主张。你二人先退下,即刻去将焚书令给朕落实下去!朕要在一月之内,看到成效!” “臣告退!” “奴婢告退!” 李斯与赵高躬身,一步步倒退着出了章台宫那高大而沉重的殿门。宫门外,秋风吹过,带着凉意。李斯面色阴沉如水,仿佛能拧出水来,他看了一眼身旁垂手而立的赵高,什么也没说,只是紧了紧袍袖,快步离去,他要去部署一场席卷全国、注定要背负千古骂名的文化浩劫。 而赵高则停留在原地,望着李斯略显仓促的背影,嘴角难以抑制地勾起一丝冰冷、得意而又残酷的弧度。他知道,经过自己这番看似替君分忧、实则火上浇油的进言,他不仅进一步巩固了在皇帝身边无人能及的地位,更成功地将骊山工程最核心、最隐秘、最可能蕴含巨大力量或秘密的部分,纳入了自己的觊觎和未来掌控的范围。一场最初或许只是为了统一思想、压制议论的行动“焚书”,因其与骊山秘密的关联,被赵高巧妙地引导,埋下了“坑儒”(清除知识阶层)乃至对工程人员进行大规模肉体消灭(“坑役”?)的恐怖种子。帝国的车轮,正沿着一条由绝对权力、深刻猜忌和残酷手段铺就的道路,隆隆向前,即将碾碎无数的文化瑰宝,也碾碎无数鲜活的生命。 历史的这一页,因骊山地底的一股暗流,而被浓墨重彩地书写上了最为黑暗的一笔。而此时,在地底深处那阴森恐怖的“净所”之中,荆、卫、梓三人,对即将降临到整个帝国文人乃至他们自身头上的巨大灾难还一无所知。他们正面临着更为直接和恐怖的生存危机。韩终得到了始皇默许甚至鼓励的“研究”,将更加肆无忌惮。那些从洪水泥泞中打捞起来的“异物碎片”,被秘密送入净所,与那些“药人”一起,成为了韩终探寻“长生”与“力量”终极奥秘的试验品。荆在一次被迫清洗沾染了黑色碎片残留物的玉碗时,惊恐地发现,那碗底残留的一丝墨绿色粘稠痕迹,在石窟壁灯幽暗的光线下,竟仿佛拥有生命般,极其微弱地、令人毛骨悚然地蠕动了一下…… 咸阳城即将燃起的焚书烈焰,试图用光明驱散思想的“迷雾”,却投下了更为深重和持久的黑暗阴影。而在地底深处,来自远古的、诡异而不祥的力量,正悄无声息地渗透进现实,与人类的贪婪、恐惧、疯狂和残酷交织在一起,酝酿着一场远超所有人想象的、足以吞噬一切的风暴。帝国的根基,正在被有形的暴政和无形的诡异力量同时侵蚀、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