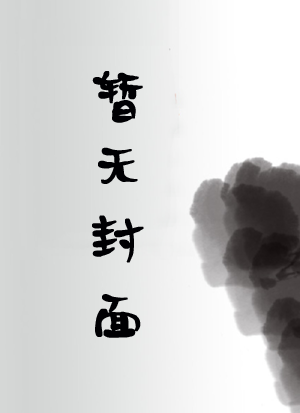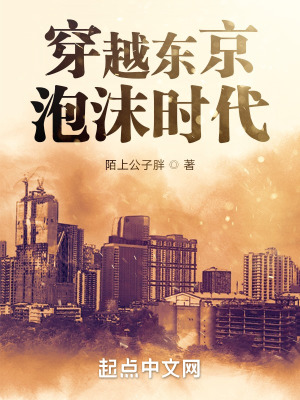第十二章:徐福东渡船队壮
第十二章:徐福东渡船队壮
咸阳宫的夏日,弥漫着一种不同于往年的燥热。渭水蒸腾起的氤氲水汽与宫殿群落的夯土气息混合,本该是盛世王朝的沉稳基调,如今却掺入了一丝难以言喻的焦灼。这焦灼的源头,深植于帝国心脏——那座日夜不息运转的庞大官僚机器的最高指令,也弥漫在丹陛之下,每一位窥伺天颜的臣子心中。
徐福一袭素净的深衣,静立在待诏的偏殿廊下,目光似乎落在庭院中一株枝叶虬结的古柏上,实则耳廓微动,捕捉着殿内传来的每一丝声响。他身形清癯,面容保养得极好,长须梳理得一丝不苟,颇有仙风道骨之姿。但若细看,便能发现他眼底深处藏着一抹难以化开的凝重。袖中手指微微捻动着一枚温润的玉珏,那是他平心静气的习惯,此刻却感觉那玉珏也带着一股莫名的寒意。
殿内,始皇帝嬴政的声音隐约传来,虽隔着重重帷幕,仍能感受到那股不容置疑的威严与……一丝几乎难以察觉的急切。是在询问骊山工程的进展。徐福的心微微下沉。自从那位同僚韩终深入骊山地底,开始那项堪称逆天的“龙脉玄机”计划后,皇帝对长生不老的渴望,仿佛被投入了滚油的烈火,燃烧得更加猛烈而失去耐心。韩终每隔一段时间送来的密报,都像是一块块砝码,不断加重着皇帝天平上对“方术”的期待,也无形中挤压着徐福这种主张“海外寻仙”的方士的生存空间。
“徐生,陛下宣召。”内侍尖细的嗓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徐福整了整衣冠,深吸一口气,将所有的情绪压入心底,脸上恢复成那种惯有的、超然物外又带着适度恭敬的神情,迈步踏入麒麟殿。
殿内熏香浓郁,金龙盘柱,始皇帝端坐于御座之上,冕旒垂旒,遮住了部分面容,但那双透过玉珠投射过来的目光,却锐利得仿佛能穿透人心。御案上,摊开着一卷显然是刚送来的密报,边角还沾着些许尘土,暗示着传递的紧急。
“徐福,”皇帝开门见山,声音平静,却蕴含着风暴前的低气压,“韩终奏报,地脉之力已初步引导,玄石与之共鸣,光华隐现,异象频生。汝常言海外仙山,蓬莱、方丈、瀛洲,有真人居焉,持不死之药。然韩生已触及天地本源,汝之仙山,究竟在何方?还需朕等待几时?”
每一个字都像锤子敲在徐福心上。他知道,韩终的“进展”无论真假,都已极大地刺激了皇帝。他不能再沿用过去那种虚无缥缈的拖延之词了。
徐福深深一揖,姿态从容不迫:“陛下圣明。韩终方士之法,夺天地造化,强引龙脉,固然惊世骇俗,然臣窃以为,此乃刚猛霸道之术。天地有常,造化有衡,强行窃取,恐非长久之道,犹如竭泽而渔,恐遭天谴反噬。臣闻近日骊山周边,地动微频,夜有异光,此或非吉兆。”
他先是以退为进,点出韩终方法的潜在风险,见皇帝眉头微蹙,并未立刻斥责,便知此言至少引起了皇帝的些许疑虑。他趁势而上,声音变得更加玄奥缥缈:“臣之所求,乃顺应天道,以诚感天。海外仙山,乃清灵之气所钟,非浊世之力可强求。需以至诚之心,备足敬献仙真之礼,更需借童男童女之纯阴纯阳未泄之体,作为灵引,方能感应仙山方位,得蒙仙人接见。此乃水到渠成之功,而非拔苗助长之举。”
他刻意将童男童女的作用提升到“灵引”的高度,而不仅仅是礼物或人口,这既符合方士理论,也为后续大规模征调提供了神圣理由。
皇帝沉默片刻,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御案:“哦?依汝之见,韩终之法不可取?” “臣不敢妄断韩生之法。”徐福连忙躬身,语气拿捏得恰到好处,“然长生之道,犹如百川归海,路径或有不同。韩生取径于地,臣求索于海。地脉之力,厚重磅礴,然易引地火;仙山之气,清虚缥缈,然得之绵长。陛下乃真龙天子,兼收并蓄,或可窥得长生全貌。只是……时机至关重要。” 他将自己和韩终摆在看似平等的“不同路径”上,既安抚了皇帝,又暗示了韩终路径的危险性,并再次强调了“时机”。 “时机?”皇帝捕捉到了这个词。 “正是。”徐福抬起头,目光清澈,仿佛能洞穿虚空,“臣近日夜观天象,见东方青龙星宿,其光渐盈,主生气勃发,利于远行探索。又感乾坤之气流转,似有通道将开之兆。此乃天时将至之象。然具体何时启航,尚需斋戒九九八十一日,于琅琊台筑坛祭天,沟通神明,方能得确切指引。” 这“九九八十一日”是他精心计算的时间。既不至于长得让皇帝彻底失去耐心,又能为他争取到足够的准备周期,同时赋予了行动极强的仪式感和不可置疑的“天意”色彩。 果然,皇帝的脸色稍霁。徐福这套结合了天象、气运、仪式的话术,听起来比韩终那种直白的地底挖掘更符合传统对“仙缘”的想象,也更能满足皇帝内心对“受命于天”的自我认知。 “既如此,朕便予你所需。童男童女、百工、船只、粮秣,一应物资,着李斯、赵高协同办理,务必充足!九九八十一日后,朕要听到仙山的消息!”皇帝最终拍板,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也有一丝被徐福描绘的“天道仙缘”所打动的期待。 “臣,领旨谢恩!定不负陛下重托!”徐福深深拜下,心中却无多少喜悦,只有一块更沉的石头落下。他知道,这只是第一步,真正的凶险,才刚刚开始。 退出麒麟殿,回到自己在咸阳的寓所,徐福屏退左右,只留下最信任的弟子侯生。烛光下,他脸上那层仙风道骨的面具瞬间卸下,露出深深的疲惫与忧虑。 “师尊,陛下已然应允,为何还忧心忡忡?”侯生不解。 徐福叹了口气,走到窗边,望向西方骊山的方向,夜色中,那座山峦如同蛰伏的巨兽。“侯生,你可知韩终在地底做的是什么?那不是求仙,那是玩火!强行抽取龙脉,激发玄石,稍有不慎,便是山崩地裂,甚至可能惊醒某些……沉睡的古老存在。陛下只看到长生有望,却看不到其下的万丈深渊。” 他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我在陛下面前所言,并非全是虚言。韩终之法,确有反噬之险。我之所以急切东渡,一方面是为完成对陛下的承诺,另一方面,何尝不是想为吾等寻一条退路?若骊山之事果真不可收拾,这咸阳,这秦土,还能安稳吗?” 侯生闻言,脸色顿时煞白:“师尊是说……” “未雨绸缪罢了。”徐福摆摆手,眼中闪过一丝算计的光芒,“东渡之事,必须加快。童男女要精心挑选,体质根骨为上,这关乎‘灵引’之效,也关乎……我们未来的根基。百工要选真正有技艺的,而非充数之辈。船只务必坚固,能抗风浪。我们要做的,不是一次简单的航行,而是一次……迁徙。” 他的话语中,透露出远超“求仙”的图谋。东渡,在他心中,已逐渐演变为一场规避潜在灾难、寻找新家园的战略转移。 与此同时,骊山地底深处,韩终并不知道徐福的谋划,或者说,他即便知道,也未必放在心上。他全身心沉浸在那诡异而强大的龙脉能量与玄石的共鸣之中。站在巨大的黑曜石祭坛上,感受着脚下传来的、如同大地脉搏般的能量流动,他心中充满了掌控一切的陶醉感。徐福那种依赖虚无缥缈“仙缘”的旧式方术,在他看来,已是过时的糟粕。力量,唯有掌握在手中的力量,才是永恒的真谛。 然而,他忽略了那些在能量通道旁呕血身亡的役夫,忽略了那些在“化生汤”中扭曲变形的“药人”,也忽略了地底深处传来的、越来越清晰的、非人的嘶吼与咀嚼声。徐福感知到的“反噬之险”,并非空穴来风。地宫的黑暗,正在孕育着连它的缔造者都无法完全控制的东西。 徐福的东渡船队,就在这种帝国上层的期待、方士内部的暗流、以及地底隐患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紧锣密鼓地筹备着。琅琊台上,船只云集,童男女的哭声与工匠的号子声交织。徐福本人则忙于斋戒、祭天,观测星象,每一次“天象示警”或“吉兆显现”,都被他巧妙利用,或调整计划,或向咸阳索要更多资源。 他的表演天衣无缝,将对长生术的“忽悠”提升到了战略层面。而这一切,都只为在那场似乎不可避免的风暴来临前,带领他的追随者,驶向未知的、却可能蕴含一线生机的大海深处。帝国的两大长生计划,如同两条开始分岔的河流,一条深入地底,试图攫取大地的核心力量,一条远赴重洋,追寻飘渺的天外仙踪,它们的终点,都将深刻地影响这个庞大帝国的命运。而历史的车轮,正沿着这条充满不确定性的轨迹,轰然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