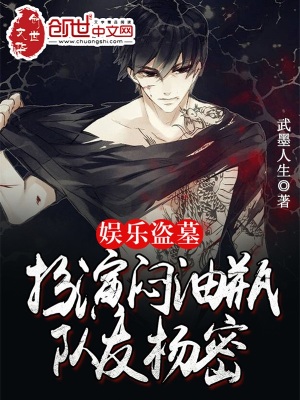一
子时未到,雪先落。
江南沈园的屋脊被白絮覆成一条沉睡的龙,檐角铜铃冻住,风撞上去,发出细碎的裂声——像谁躲在回廊阴影里,偷偷咬碎了一枚冻硬的玉簪。园子里静得反常,连巡夜家丁的梆子声都没了踪影,只有更鼓从十里外的府县城墙根飘过来,一声,两声,鼓面裹着湿雪,闷得像把冬夜的寂静砸出一个个浅坑,坑底又迅速被新雪填满。
沈砚把窗推开半指宽的缝,雪光立刻挤进来,刀似的贴在他眼皮上。十五岁的少年骨架还没长开,袖口空荡得能塞进半只拳头,却不怕冷——他自小在江南的湿寒里长大,冬日里常赤手翻父亲书房的旧卷,指尖早练出一层薄茧,连砚台里结的冰都能徒手化开。但今夜,他怕的不是冷,是雪光里藏着的那股腥气:铁锈味混着佛手柑的尾调,像有人把父亲案头那盏沉香炉里的灰,倒进了刚凝的血里。
这股味道,他傍晚时就在父亲沈伯夷身上闻到了。那时父亲刚从府城回来,玄色织金袍的下摆沾着雪,却没沾半分泥——仿佛不是从车马喧嚣的官道回来,是从云端落下来的。他递过一本卷边的《星象考》,指尖蹭过沈砚的手背,凉得像冰,却又带着一丝古怪的烫,就像此刻袖中那枚被锦帕裹着的东西,冷热交织,像揣了颗活物的心脏。
“别开窗。”身后传来沈七的声音,压得极低,像怕惊飞了屋梁上积着的雪。
沈砚没回头,指尖在窗棂上摩挲。那是沈家祖传的沉香木,百年不腐,木纹里藏着浅淡的星斗纹——父亲说过,这是祖父年轻时请天机门的木匠刻的,天机门的人最懂“藏”,能把机关刻进木纹,把秘密藏进沉默。可此刻,这坚硬的木头却像被虫蛀空的旧牙,一碰就掉木屑,簌簌落进雪里,瞬间被吞没,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
“再不开,屋里的灯油就要耗光了。”他说。声音很轻,却带着少年人特有的执拗。他知道沈七在怕什么——从傍晚开始,府里的家丁就少了一半,厨房的老周叔没再来送夜宵,连平日里总爱绕着回廊跑的大黄狗,也没了踪影,只有狗窝旁那根啃剩的骨头,还沾着点肉沫。
“耗光总比被外头的东西看见强。”沈七走过来,手里攥着一盏风灯。灯罩裂了道斜纹,火舌从裂口里窜出来,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影子比真人胖三倍,脑袋却瘦成一条缝,像被门夹过的纸人,歪歪扭扭的。沈七的棉袄前襟湿了一大片,不是雪水,是汗。腊月廿三,冷得连井沿都结了冰棱,他却汗透重衣,连鬓角的白发都黏在脸上,像刚从蒸笼里出来。
沈砚终于回头,看见沈七的手在抖。那双手沈砚从小看到大,粗粝得像砂纸,却能精准地给父亲的古琴上弦,能把铜钱穿成整整齐齐的串,连穿线的孔都对着同一个方向。可现在,这双手攥着风灯的提杆,指节泛白,连灯罩上的裂纹都跟着颤,仿佛下一秒就要把灯摔在地上。
“你去了哪里?”沈砚问。
沈七不答,把风灯放在案上。灯油晃了晃,火舌舔了舔灯罩,映出案头那本《水经注》——书页被雨水泡过,边缘发毛,像一排被啃坏的牙。这是母亲去年给沈砚的生辰礼,母亲说:“读遍水经,就能走遍天下,将来阿砚要去看看黄河的浪,塞北的雪。”可沈砚现在连沈园的门都不敢出,连窗外的雪都不敢多看一眼。
“老爷让我交给少爷。”沈七的声音瘪在嘴里,像被雪堵住了喉咙。他从怀里掏出一个锦帕包,递过来时,沈砚看见他袖口沾着一点蓝——不是染布的靛蓝,是像霜一样的东西,一碰就化,指尖还留着点凉。
锦帕掀开,是一枚罗盘。
巴掌大,铜质,却轻得像一片干叶。盘面没有指针,只有五道裂痕,裂痕里嵌着极细的蓝丝,随沈砚的呼吸明灭:他吸气时,蓝丝就亮一点,像醒了;呼气时,就暗一点,像睡了,仿佛在和他的性命相连。沈砚用指腹去碰,蓝丝立刻爬向他的指尖,冰凉的触感里裹着一丝烫,像触到了刚熄的炭火,他猛地一缩手,蓝丝却没断,还在指尖绕了个圈,像在打招呼,又像在缠人。
“玄玑?”他低声道。这两个字是从父亲的书里看来的,《玄玑秘录》的扉页上写着“天地有气,名玄玑,可定山河,可乱乾坤”,但父亲从不许他多问,只说“那是江湖人的东西,与我们沈家无关,沈家只做读书人家”。
沈七的汗滴在罗盘上,蓝丝竟像活物似的避开了那滴汗,往沈砚的方向缩了缩,仿佛嫌沈七的汗脏。沈七的喉结上下滚了滚,又说:“老爷还说,如果……如果他没回来,少爷就带着它,从水门走,一直往北,别回头。”
“水门”两个字刚出口,窗外忽有鸦声,凄厉得如同裂帛。那只鸦就停在院中的梅枝上,羽毛被雪染白了一半,却盯着沈砚的窗户,眼睛是红色的,像浸了血,连眨都不眨。
沈砚猛地合拢窗扇,鸦声戛然而止。他靠在窗上,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比更鼓还响——父亲从不说“如果”,他是个做事笃定的人,连下棋都从不悔子,连给沈砚讲书都要把每个字的出处说清楚。今夜,他却用了“如果”,像在交代后事。
二
雪更密了,风却停了。
沈园的灯笼一盏盏熄灭,最后只剩书斋这方格子还亮着。风灯的火舌稳定下来,映得案上的罗盘蓝丝更亮,像把夜空里的星斗摘了几颗,嵌在铜盘里,冷得晃眼。沈砚把罗盘塞进袖袋,袖子里还有他的小世界:半块没吃完的松子糖(是母亲下午给的,还带着桂花味,糖纸是油纸做的,印着小莲花)、一枚平安符(母亲绣的,里面裹着晒干的艾草,针脚很密,边缘还锁了花)、还有那本《水经注》。他把书抱在怀里,书页的温度让他稍微安心了点——母亲的手温,好像还留在纸上。 他推门,门轴发出一声长叹,像老人咳嗽,在寂静的园子里格外清楚。廊下的积雪没到脚踝,踩上去“咯吱”响,每一声都像踩在棉花上,软得发虚。积雪上印着凌乱的脚印,大多朝向西厢(那是家丁和仆妇住的地方),只有一行,往东厢——东厢是父亲的书房,夜里从不点灯,父亲说,他要在黑暗里“听纸说话”,纸里藏着前人的心思,亮灯了,心思就跑了。 沈砚的脚印刚踩上东厢的第一级台阶,书房的窗忽然亮了。不是烛火的暖黄,是罗盘里那种蓝,冷得像冰,却又带着穿透力,把窗纸都染成了蓝色,连窗棂的影子都变成了蓝的。紧接着,一声“咔”——像谁掰断了一根脆骨,轻得几乎听不见,却让沈砚的后背瞬间爬满冷汗,连头发都竖了起来。 蓝光骤灭。 沈砚的呼吸卡在嗓子眼,他想起父亲傍晚那句话:“纸会说话,也会吃人。”那时他没懂,只觉得父亲在说笑话,纸怎么会吃人?现在却突然明白了——父亲书房里藏着的,可能不是纸,是能吃人的秘密,是连灯都不敢照的东西。 他抬手,袖口里的罗盘在跳,一下,两下,像颗小小的心脏,撞得他手腕发麻。那跳动的节奏,和东厢里的动静,竟隐隐相合——像是在呼应,又像是在求救,隔着一扇门,一颗心在里面,一颗心在外面,互相找着对方。 三 书房门虚掩着,雪片从门缝钻进去,瞬间没了声息,仿佛被屋里的东西吞了。沈砚伸手,指尖刚碰到门板,里头先传来“咕咚”一声——重物坠地的声音,闷得像砸在棉花上,连地板都没震一下,却让沈砚的膝盖发软。 血腥味扑面而来,甜得发腻,比傍晚闻到的更浓。沈砚的指尖发抖,他想起小时候,父亲带他去田埂上看农人杀猪,猪血的腥味是咸的,带着土气;可今夜的血,是甜的,像加了蜜的毒,闻多了头晕,连眼睛都发花。 门被风顶开,雪地反射的冷光灌进屋子,照出地上的人——沈伯夷。他没穿素日常着的青布直裰,而是穿了那件沈砚傍晚见过的玄色织金袍,袍角绣着扭曲的星斗,金线在血泊里泡成了黑线,像一条条死蛇,缠在他的腿上。他的脸朝地,右手却拼命朝门口伸,食指断了一截,断口处缠着蓝丝,像一群细小的蚂蚁在搬运月光,把血都染成了蓝色,连地上的青砖都沾了点蓝。 沈砚扑过去,膝盖砸进血泊,冰凉瞬间穿透棉裤,渗进皮肤,冷得他打了个寒颤。他想把父亲扶起来,却发现父亲的身体沉得像灌了铅,玄色的袍子吸满了血,重得扯不动,仿佛衣服里裹着的不是人,是块石头。 “爹!”他喊,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连自己都快认不出了。 沈伯夷的瞳孔已经散了,却硬撑着最后一口气,眼珠往沈砚的袖口转——那里,罗盘的蓝丝正透过布料亮起来,和他伤口里的蓝丝,像隔着距离的亲人,互相召唤,蓝丝亮一下,父亲的眼皮就颤一下。 “……别……信……”他的嘴唇动了动,声音轻得像雪落,风一吹就散。 信什么?信谁?沈砚没来得及问,沈伯夷的瞳孔里忽然映出第三只手——苍白,瘦长,指甲修剪得极整齐,连边缘都磨得光滑,从书架后的暗格里伸出来。那只手里捏着一片薄如蝉翼的铜叶,铜叶边缘滴着血,血珠落在地上,竟没化开,而是凝成了小小的冰粒,像碎掉的星星。 那只手把铜叶按在沈伯夷的后颈,蓝丝“嗤”地窜进皮肤,像缝衣线被拉紧,沈伯夷的脑袋诡异地仰起,嘴角竟扯出一抹笑——不是痛苦的笑,是释然的,甚至带着点期待的笑,仿佛终于完成了什么事,终于能松口气了。 下一秒,书架轰然合拢,暗格消失,连一点缝隙都没留下,仿佛从未存在过。书架上的书掉下来,砸在地上,却没有声音,像掉在棉花上——不对,是掉在蓝雾里,书刚碰到地面,就被一层薄蓝雾裹住,慢慢化了,连纸渣都没剩下。 沈砚的袖口一空——罗盘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道猛地抽走!他回头,只看见半片玄色衣角掠出窗外,那衣角上的星斗纹,和父亲袍角的一模一样,连金线的粗细都没差。雪地上没有脚印,甚至连衣角扫过雪面的痕迹都没有,仿佛那个人是飘着走的,脚根本没沾地。 四 园子深处传来第一声惨叫,是厨房的老周叔。那声音刚出口就断了,像被什么东西捂住了嘴,只剩下闷闷的“唔”声,然后是重物落地的声音,轻得像一片叶子掉下来。 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像有人依次点燃一串爆竹,却用雪捂住了炮仗,爆裂声变成钝钝的“噗”“噗”,每一声都砸在沈砚的心上,砸得他喘不过气。他踉跄着追到院中,雪片打在脸上,化成水,水又变热——他摸了摸脸,是鼻血,不知何时流出来的,滴在雪地上,红得刺眼,像一朵开在雪地里的红梅。 西厢的火光最先蹿起,火舌舔着窗棂,发出婴儿啼哭般的噼啪声。沈砚看见母亲站在火光里,她穿一件月白小袄,披头散发,头发上还沾着雪,却没融化——母亲的头发是暖的,雪落在上面,该化的。她手里抱着那架焦尾琴,那是父亲给母亲的定情物,琴尾有一道裂痕,是母亲当年学琴时不小心摔的,父亲说“裂了才好,有了念想,琴就有了魂”。 琴弦全断了,拖在地上,像一条被剥了皮的蛇,软塌塌的。母亲赤足踩在雪里,雪没到她的脚踝,却没融化——她的脚是凉的,比雪还凉,连雪都怕她。足踝上环着一圈蓝丝,那丝线正往她的皮肤里钻,所过之处,皮肤变得透明,能看见底下青紫的血管,像冻住的藤蔓,缠在骨头里。 “阿砚,”母亲对他笑,声音却像从很远的水底传来,模糊不清,像隔着一层厚厚的冰,“你爹让你走水门,你怎还不走?”她的嘴唇没动,声音却飘过来,像风里的回声,分不清是真的,还是沈砚的幻觉。 沈砚朝她奔去,脚下一滑,整个人扑进雪堆,脸埋进冰冷的甜腥里。雪钻进他的鼻子,冷得他想打喷嚏,却不敢——怕惊动了什么。他想爬起来,却被雪冻住了手脚,只能看着母亲转身,朝火里走。火舌卷上她的发梢,发梢竟没烧起来,只滴下蓝色的珠子,一落地就结成冰,像一串碎掉的星星,滚到沈砚的脚边,凉得刺骨。 “娘——!”他的喊声被头顶一声锐响割断。 他抬头,看见园中最老的那株梅树。红梅开得正盛,被雪压弯了枝丫,枝头却悬着一个人——沈七。他的脖子被白绫勒住,白绫另一头系在梅枝上,枝丫承受不住重量,“咔嚓”一声折断,沈七的尸体直直砸下来,落在沈砚面前,雪溅了他一脸。 尸体的左手紧攥着,指缝间露出锦帕的一角——那本该裹着罗盘。沈砚掰开他的手指,指关节硬得像石头,费了好大劲才掰开,里面却只剩一团雪,雪里裹着半片断甲。断甲上刻着扭曲的星斗纹,和父亲袍角、那抹玄色衣角上的,一模一样,连星斗的位置都没差。 沈七的眼睛睁着,瞳孔里映着梅树的影子,影子上缠着蓝丝,像一张网,把梅树的影子都网住了。他的嘴角还沾着点血,血是蓝的,像罗盘里的丝。 五 火借风势,很快连成一片。雪不化,火不灭,两种极端在沈园里撕扯,蒸腾出诡异的蓝雾。雾里带着甜腥气,吸一口就头晕,像被灌了劣质的酒,连脚步都站不稳。 蓝雾里,有人影绰绰。他们都穿着玄衣,衣料很薄,却不怕冷,雪落在上面就滑下来,不留痕迹,仿佛衣服是用冰做的。每个人都戴着铜面具,面具上凿出五个孔——两个眼孔,一个鼻孔,两个嘴孔,孔里嵌着蓝丝,像把夜空里的星斗硬摁进人脸,冷得吓人。 他们手里提着木桶,桶里不是水,是油——油面浮着蓝火,火不热,反冒寒气,靠近一点就觉得指尖发麻,像触到了冰。他们走到哪里,火就灭到哪里,留下一地冰渣,冰渣里嵌着细小的蓝丝,像没化的雪,踩上去“咯吱”响。 沈砚躲在假山后,假山是祖父建的,石头缝里藏着他小时候的秘密——他曾在这里藏过一只受伤的麻雀,后来麻雀飞走了,留下一根羽毛,他一直没舍得扔,现在还藏在怀里。此刻,他攥着那根羽毛,羽毛的温度让他稍微清醒一点,知道自己还活着,不是在做梦。 他听见面具人说话,声音像钝刀刮铜,断断续续,每个字都磨得耳朵疼: “……罗盘……碎片……主家……要……” “……沈家……不留……活口……” “……水门……堵死……别让……跑了……” 水门!沈砚的喉头动了动,袖中突然一沉——那枚罗盘竟又回来了!不知何时被谁塞回了袖口,冰凉地贴着他腕内的脉搏,像一条冬眠的蛇被心跳惊醒,慢慢活了过来。他摸了摸,罗盘还在,蓝丝比之前更亮了,五道裂痕里,竟隐隐有第六道在慢慢裂开,细得像头发丝,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罗盘在“指北”——如果那蓝丝算指针的话。可蓝丝却疯狂打转,转了三圈,最后定在一个古怪的方向:东北偏北。那里是沈园的粪厕,平日连狗都不肯靠近,墙根下有一道被杂草遮住的泄水沟,沟窄得只能容少年的肩宽,通向外面的河——那是沈砚小时候偷偷摸鱼发现的,父亲知道后,没骂他,只说“这是沈家的水门,不到万不得已,别用”。 他猫腰钻进草丛,草上的雪落在脖子里,冷得他一哆嗦。身后传来脚步踩碎冰渣的“咯吱”声,每一步都像踩在他的脊梁上,越来越近。他不敢回头,只能往沟的方向爬,杂草刮破了他的手,血滴在雪上,立刻被蓝雾裹住,变成了蓝色的小珠子,像罗盘里掉出来的丝。 六 泄水沟比记忆中更窄,青苔滑腻得像肥皂,沾在手上甩不掉,像无数冰凉的小手在拖他的后腿。沟里的水很臭,混着粪水和雪水,溅在脸上,他却不敢擦——怕发出声音,怕被面具人发现。 罗盘在他前面飘——不是比喻,是真的飘。铜盘脱离了他的掌心,贴着沟底的水流往前滑,蓝丝在水里拖出细长的尾光,像一群发情的水蛇,照亮了沟壁的砖缝。沈砚跟着罗盘爬,水没过了他的膝盖,冷得他牙齿打颤,却不敢停,连呼吸都不敢大声,怕呛到水,怕发出咳嗽声。 身后,火光忽然暗了,脚步声也停了。沈砚刚松了半口气,头顶的沟盖“咣”地被掀开,一张铜面具探下来。面具的眼孔里,蓝丝同时伸长,像两条毒蛇,直插水面,离他的脸只有一寸远——他甚至能看见蓝丝里裹着的细小冰粒,像毒针。 “找到了。”面具后的人笑,声音像两块锈铁互相摩擦,刺耳得很。蓝丝碰到了沈砚的头发,冰凉的触感让他头皮发麻,连头发都竖了起来。他猛地潜入水底,水脏得发黑,却能看见蓝丝在他眼前炸开,像一朵发狂的海葵,每一根丝都在找他身上的罗盘,绕着他的胳膊、腿转,像要把他缠起来。 避无可避,沈砚张嘴,一口咬断了离自己最近的那根蓝丝。腥甜味灌满了口腔,蓝丝竟像血一样热,烫得他舌头发麻。断口处喷出一小簇火,火在水里燃着,照亮了他眼前的一瞬—— 他看见沟壁的砖缝里,嵌着一块铜叶,和之前那只手捏着的铜叶一模一样,连边缘的弧度都没差。铜叶上刻着字,很小,却很清晰,是篆体:“非沈氏血,不可启。” 铜叶的边缘,卡着一截断指——是父亲的,沈砚认得,父亲的食指上有一道疤,是去年修书架时被木刺扎的,他还帮父亲涂过药膏,疤的形状他记得很清楚。断指还保持着屈扣的姿势,像在死死按住什么,怕里面的东西跑出来。 沈砚伸手,把断指掰下来。断指一离开铜叶,就化成了一撮蓝灰,灰里落下一把极小的铜钥匙——只有指甲盖那么大,上面刻着星斗纹,和父亲袍角、断甲、铜叶上的星斗,一模一样,连星斗的数量都没差。 钥匙落入他掌心的瞬间,罗盘突然疯转,沟里的水倒卷,形成一个小小的漩涡,把他整个人吸了进去。他失去了意识,最后看见的,是罗盘的第六道裂痕彻底裂开,蓝丝从缝里钻出来,缠上了那把铜钥匙,像给钥匙系了条蓝丝带,再也分不开。 七 再睁眼时,他已经躺在河滩上。雪还在落,却比沈园的雪软,落在脸上,化成水,凉丝丝的,让他清醒了不少。身后,沈园的方向火光冲天,照得夜空呈诡异的靛紫,像有人打翻了染缸,把黑夜染成了彩色,连雪都沾了点紫,像撒了把碎宝石。 沈砚爬起身,第一件事是摸袖口——罗盘在,钥匙也在。罗盘的蓝丝缠在钥匙上,像长在了一起,扯都扯不开。他松了口气,却又觉得胸口发闷,忍不住弯下腰呕吐。吐出来的不是脏水,是一团蓝丝,那丝在雪地上扭动,竟要往雪里钻,像想逃回沈园的方向,像想回到那些面具人身边。 沈砚捡起一块石头,狠狠砸下去。蓝丝发出婴儿啼哭般的“吱”声,尖得刺耳,才不甘心地化成一滩黑水。黑水渗入雪地,留下五个小孔,排列成星斗的形状——和父亲袍角、断甲、铜钥匙上的星斗,一模一样,连孔的大小都没差。 他抬头,河对岸的芦苇丛里,不知何时立了个人。白衣,披发,头发很长,垂到腰际,被雪染白了几缕,像沾了霜。那人手里提着一盏圆圆的风灯,灯罩是白色的,没有画任何字画,却自内里透出蓝火——和罗盘、和面具人铜叶里的蓝火,一样的颜色,一样的冷。 那人隔河对他弯腰,行了一个很浅的礼,像戏台上的伶人向看客致意。他的动作很轻,雪落在他的肩上,竟没留下痕迹,仿佛他不是真人,是雪做的,是风做的,一触就散。 沈砚眯起眼,想看清那人的脸,却只看见一片模糊——像是被蓝雾挡住了,又像是他的眼睛花了,怎么都看不清。那人把风灯轻轻放在冰上,灯底压着一张对折的纸。放完,他后退一步,没入芦苇丛。芦苇秆一根根折断,像被无形的手掰断,为他让出一条无声的通道,没有一点声音,连芦苇叶摩擦的声都没有。 沈砚踏冰过河。冰面很薄,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怕掉下去,怕掉进冰冷的河里。风灯没倒,纸也没湿,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护着它们,不让雪碰,不让冰化。他拿起纸,展开——上面只有一行字,墨迹未干,被雪光映得发亮:“沈氏死绝,罗盘方活。” 字迹他认得,是父亲的亲笔。父亲的字是柳体,笔锋刚劲,每个字都站得很直,像父亲本人。可这行字的最后一笔却多了一钩,那一钩像一把刀,把纸都划破了,露出底下的纤维——纸是宣纸,质地细腻,是竹隐盟的人常用的那种纸(父亲曾说过,竹隐盟的文人爱用这种纸写诗句,因为吸墨,写出来的字有筋骨),可父亲从不和竹隐盟的人打交道,他说“江湖人太乱,我们沈家要守着本分”。 八 沈砚把纸揉成团,塞进怀里,和罗盘、钥匙贴在一起。冷与热同时袭来,他打了个哆嗦,抬头看天。雪忽然停了,云幕拉开,露出一颗星——星色发蓝,正是罗盘裂痕里那种蓝,亮得刺眼,像在盯着他看,像在指引他方向。 星光照在河面上,照出他的影子。他的影子比他本人长出一截,那多出的一截,正从袖口延伸出来,像另一条手臂。那条“手臂”里,握着什么东西,微微闪光——是那把铜钥匙,钥匙上的星斗纹,在星光下亮得很。 沈砚低头,自己的手里空无一物。他再抬头,影子却把钥匙举高了,对他晃了晃,像在炫耀,又像在提醒他什么。影子的嘴角裂到耳根,牙齿是细密的蓝丝,一根根,像罗盘里的丝,在星光下发亮,笑得吓人。 沈砚猛地甩袖,影子被抖碎,化成一圈圈涟漪,消失在冰下。冰面恢复了平静,却映出他的脸——他的眼角,不知何时多了一点蓝,像沾了蓝丝,擦不掉,洗不净,像一颗小小的星,嵌在皮肤里。 他摸了摸眼角的蓝,不疼不痒,却很凉,像罗盘的温度。 九 他转身,朝北。父亲说过,一直往北,别回头。他不知道北边有什么,只知道父亲让他去,他就去——父亲从不骗他,父亲说的话,都是对的。他的鞋湿了,踩在雪地上,每一步都很沉,却很坚定,像父亲教他走路时那样,抬头,挺胸,别弯腰。 第一步刚踏出,身后沈园的方向传来“轰”一声巨响。火光灭了,雪又开始下,大片大片,像有人在天上撕棉絮,砸在地上,发出“簌簌”的声,盖过了一切动静。巨响之后,是死寂——连鸦声都没有了,连风声都没有了,只有雪落的声音,轻得像梦。 沈砚没回头,却听见“咔”的一声轻响——从他自己的袖中传来。他低头,看见罗盘的第六道裂痕里,探出一截极细的蓝丝。那丝翘起来,对他摇了摇,像一根手指,在招呼他过去,又像一条蛇,在嗅他的气味,在确认他是谁。 他攥紧了拳头,把罗盘和钥匙攥得更紧。指尖传来罗盘的跳动,和他的心跳合在一起,像两颗心,在共同跳动,在共同往前走,再也分不开。 十 雪地上,沈砚的脚印很快被新雪填平。只有一行脚印例外——那脚印比他的小,赤足,五趾清晰,每一步都踩在他脚印的正中,像孩子踩着大人的影子做游戏,像有人在跟着他,却又不想让他发现。 脚印延伸向北方,尽头消失在河堤下。堤下,那盏白色的风灯静静躺着,灯罩裂了,蓝火已经灭了,灯底却多出一枚小小的铜叶——和沟壁上的、面具人手里的,一模一样,连刻字的力度都没差。 铜叶上,新添了一滴血。血珠滚到叶缘,停住,不坠。血珠里,映出沈砚远去的背影——他的袖口,一截蓝丝正悄悄探出,在风中轻轻摇晃,像一条嗅到猎物气息的蛇,像一颗醒着的星,在黑暗里亮着。 沈砚走了很远,才想起回头。他看见河堤下的风灯,看见那枚铜叶,看见那行赤足的脚印。他想回去看看,想知道是谁留下的铜叶,是谁跟着他,却觉得罗盘在拉他,往北边拉,像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他,像父亲在北边等着他。 他继续走,北边的天空,那颗蓝色的星,更亮了。雪落在他的肩上,化成水,又结成冰,他却不觉得冷——袖中的罗盘,正暖得像一颗心,陪着他,往北走,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