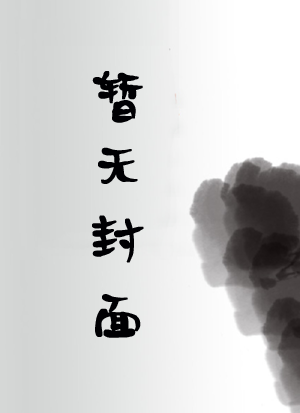第14章:祸水东引
【麻烦来了!】
【福安这是奉命来试探警告的!】
【张公公果然盯着呢!】
“福安哥您这可冤死奴才了!”李诚叫起屈来,“奴才对张公公的忠心天地可鉴!只是娘娘问话,奴才不敢不答,但奴才句句都是维护张公公的啊!您若不信,可以去问娘娘宫里的碧荷姐姐!”
他故意把碧荷抬出来,既是增加可信度,也是想把水搅浑。
福安将信将疑地盯着他,冷哼一声:“最好如此。别忘了,你能有今天,是谁给你的!干爹能把你捧上来,也能把你踩下去!给我放聪明点!”
说完,他用力撞了一下李诚的肩膀,扬长而去。
李诚揉着发痛的肩膀,看着福安的背影,眼神逐渐冰冷。
张公公的警告来得又快又直接。这说明淑妃宫里有他的眼线,也说明张公公确实对自己与淑妃的接触极为敏感和忌惮。
回到御书房附近,李诚发现气氛有些异样。几个小太监聚在一起窃窃私语,见到他过来,立刻散开,眼神古怪。
张公公面色阴沉地站在廊下,见他回来,冷冷道:“小诚子,你过来。”
李诚心中升起不祥的预感,快步上前:“公公有何吩咐?”
张公公盯着他,一字一顿地问道:“方才,你是否碰过陛下案头那方‘青龙献瑞’的端砚?”
青龙献瑞端砚?那是皇帝心爱之物!
李诚心里咯噔一下,连忙道:“回公公,奴才今日未曾碰过那方砚台。奴才只负责研墨,取用的都是常用的那方紫石砚。”
“未曾碰过?”张公公眼神锐利,“那为何砚台底部,发现了一道新的裂纹?今日除了你,还有谁接近过御案?”
李诚的冷汗瞬间就下来了!又是栽赃?!这次竟然是直接陷害他损坏御用之物!
“公公明鉴!奴才真的未曾碰过!”他急声辩解,“今日陛下批阅奏折时,奴才一直在旁伺候,并未见异常。可否让奴才看看那裂纹?”
张公公冷哼一声,带着他走进内殿。御案上,那方精美的青龙献瑞端砚被单独放在一旁,底部朝上。果然,在龙尾处,有一道细如发丝的裂纹,不仔细看几乎无法察觉。
【碰瓷!绝对是碰瓷!】
【这裂纹太新了,像是刚刚故意敲出来的!】
【张公公这是要下死手了啊!】
李诚大脑飞速运转,他知道,单纯的辩解是苍白的。他必须找到证据,或者,将嫌疑引向别处。
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仔细观察那方砚台和周围的桌面。忽然,他目光一凝,注意到砚台旁边,掉落着一点点极细微的……深绿色碎屑?
这不是墨渣,也不是灰尘。他小心翼翼地用手指沾起一点,凑近鼻尖闻了闻——有一股极淡的、类似铜锈的味道?
与此同时,弹幕提供了关键线索:
【这碎屑……好像是某种玉石或孔雀石打磨时掉落的?】
【看裂纹走向,不像是磕碰,倒像是被某种尖锐的东西从内部硌了一下?】
【快看御案笔洗里!那支最大的狼毫笔的笔杆顶端,是不是嵌了一小块凸起的绿松石?】
李诚猛地转头看向笔洗!果然,那支皇帝用来批阅重要奏章的特制狼毫笔,笔杆顶端镶嵌着一小块装饰用的绿松石,而那绿松石的一个尖角,似乎有细微的磨损痕迹!
一个大胆的推测在他脑中形成。
他转向张公公,语气带着不确定和一丝“恍然大悟”:“公公……奴才或许知道这裂纹是怎么来的了!”
“你知道?”张公公眼神一厉,语气带着压迫,“说!若有半句虚言,罪加一等!”
殿内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李诚身上,空气仿佛凝固了。福安在一旁嘴角噙着一丝冷笑,等着看好戏。
李诚深吸一口气,指向笔洗中那支狼毫笔,语气带着几分不确定的推测,而非肯定的指证:“公公请看那支笔。笔杆顶端的绿松石,似乎有个尖角磨损了。而砚台底部这裂纹旁,又有些许深绿色碎屑……”
他顿了顿,看向皇帝平日批阅奏折时御案上的布局,继续道:“奴才斗胆推测,是否陛下批阅奏折至激动处,悬腕运笔时,笔杆顶端的绿松石无意中重重磕碰或硌到了砚台底部?因力道角度刁钻,致使砚台内部产生细微裂纹,而绿松石也因此崩落碎屑?此事纯属意外,若非仔细查验,极难察觉。”
他这番话,避重就轻,将“人为损坏”巧妙转化为“意外磕碰”,既为皇帝可能的“激动”留下了体面的解释,又指出了确实存在的物证(绿松石碎屑和磨损),并将自己的嫌疑撇清——他只是个研墨的,碰不到笔杆顶端。
【精彩!祸水东引…啊不,是合理推测!】
【把锅甩给皇帝自己的操作,妙啊!】
【既解释了裂纹来源,又保住了皇帝的颜面!】
张公公脸色微变,立刻上前拿起那支狼毫笔仔细查看,又对比砚台裂纹旁的碎屑。果然,颜色、质地都极其相似!他再回想皇帝近日因北方军务确实时常动怒,运笔力道加重……这个解释,在逻辑上完全说得通!
若他再强行诬陷李诚,反而会显得刻意,甚至可能被反咬一口诬告!
皇帝不知何时已停下了朱笔,目光淡淡地扫过砚台和笔杆,脸上看不出喜怒。但熟悉他性情的张公公知道,陛下这是听进去了,并且对这个“意外”的解释,至少没有立刻否定。
张公公反应极快,立刻顺势而下,脸上堆起懊恼和庆幸的表情:“原来如此!竟是这般缘由!老奴眼拙,险些错怪了小诚子!万幸陛下洪福,宝砚只是微损,无伤大雅。倒是老奴御下不严,惊扰圣驾,请陛下恕罪!”
他轻飘飘一句话,就把自己摘了出来,把事件定性为“意外”和“自己关心则乱”。
皇帝沉默片刻,才缓缓开口,声音听不出情绪:“一方砚台而已,碎了也就碎了。日后当差,都仔细些。张伴伴,你也是宫里的老人了,遇事莫要急躁。”
“是是是,老奴谨记陛下教诲!”张公公连忙躬身应道,后背却惊出了一层冷汗。皇帝这话,看似宽容,实则暗含告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