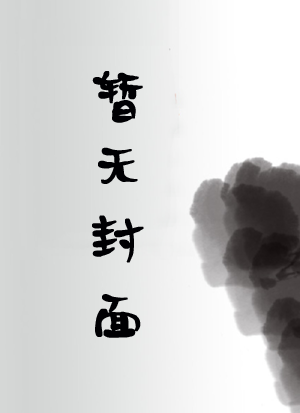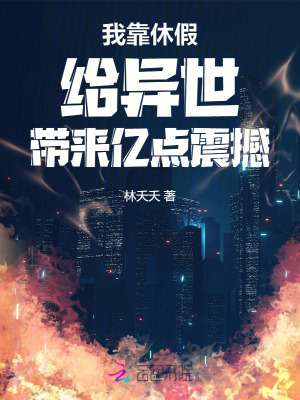第20章:陷入迷茫
李诚的心再次提起,脸上却露出恰到好处的“茫然”和“敬畏”:“是……是吗?奴才孤陋寡闻,竟不知马老将军与奴才是同乡。奴才这等微末之人,岂敢与将军相提并论。”他完美扮演了一个因与大将军同乡而感到惶恐荣幸的小人物。
皇帝放下茶盏,目光投向窗外,语气带着一丝难以捉摸的意味:“是啊,悍卒……多是直性子,不懂变通,容易得罪人,也容易……被人惦记。”
这话听起来像是感慨,但落在李诚耳中,却如惊涛骇浪!皇帝这话,是在说马彪?还是在影射他的父亲李啸云?他是否对当年的西北旧案,也心存疑虑?
李诚不敢接话,只是将头埋得更低,屏息凝神。
殿内陷入短暂的沉默,只有更漏滴答作响。
良久,皇帝收回目光,重新拿起朱笔,仿佛刚才只是随口闲聊,挥了挥手:“退下吧。”
“是,奴才告退。”李诚如蒙大赦,恭敬地退出内殿,直到走出很远,才发觉自己内衣已被冷汗完全浸透,双腿都有些发软。
这次问话,看似有惊无险地度过了,但皇帝话语中透露的信息,却让李诚心潮难平。
皇帝记得陇右,记得马彪,甚至对“悍卒直性子易得罪人”有感慨……这是否意味着,皇帝内心对当年李啸云案,并非全然深信不疑?或者,他只是在感慨边将难用?
无论如何,皇帝的目光已经更多地投注到了他的身上。这既是危险,也可能蕴含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当天傍晚,李诚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住处,思绪依旧纷乱。他需要将皇帝的问话和马彪提供的信息结合起来思考。
就在他准备休息时,窗外再次传来了三声熟悉的叩击声。
是马奎!
李诚立刻开窗。马奎闪身而入,神色比上次更加凝重。
“将军让我告诉你两件事。”马奎语速极快,“第一,你预感的没错,今日午后御药房确实有异动,有生面孔试图接近那老太监,被我们的人惊走了。对方很警觉,没留下痕迹。” 李诚心中凛然,果然不是错觉! “第二件事,”马奎压低声音,“将军通过旧部查到,赵德明暴病身亡前,曾将其子赵铭托付给一个京城的老镖师,并留给他一个铁匣子,嘱咐非到万不得已不得开启。那老镖师几年前也已去世,铁匣子下落不明。” 铁匣子!这很可能就是赵德明留下的后手,里面或许有揭露真相的证据! “能找到那铁匣子吗?”李诚急问。 马奎摇头:“很难。但将军怀疑,赵铭可能知道些什么,甚至可能暗中在寻找那个铁匣子。你若要接触他,或可从这点入手。” 这无疑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新线索! 送走马奎,李诚心绪难平。皇帝的试探,御药房的杀机,赵铭身上的铁匣子线索……信息纷至沓来。 他正沉思间,房门被轻轻敲响,门外传来一个小太监的声音:“小诚子,张公公让你去一趟,说是有批新到的贡墨,让你去认认品质。” 张公公?又是晚上召见?李诚心中一紧,有种不祥的预感。 他应了一声,整理了一下衣袍,深吸一口气,走向张公公的值房。 值房内,张公公正拿着一块墨锭对着灯看,见他进来,笑了笑:“来了?看看这墨,色泽黝黑,触手细腻,是上好的徽墨。” 李诚上前恭敬接过,假装仔细观看,心中却警惕到了极点。 张公公状似无意地问道:“小诚子,今日陛下跟你聊起老家了?” 李诚的手微微一颤,果然!皇帝身边的任何风吹草动,都瞒不过张公公! 他稳住心神,将白天对皇帝的说辞又重复了一遍,脸上带着受宠若惊的惶恐。 张公公听着,脸上的笑容意味深长:“陇右道啊……那可是个好地方。说起来,淑妃娘娘的母亲,祖籍也是陇右呢。说不定,几百年前,你们还是同乡。” 淑妃的母亲……也是陇右人? 张公公这话,是随口一提,还是意有所指?是在暗示淑妃势力与陇右的关联,还是……在警告他不要与某些“同乡”走得太近? 李诚感觉自已仿佛陷入了一张由籍贯、往事、利益交织成的巨大迷网之中,每一步都可能触发未知的机关。 张公公那句关于“淑妃母亲祖籍陇右”的话,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在李诚心中漾开层层涟漪。这仅仅是巧合,还是暗示着淑妃家族与西北旧案有着更深的地域渊源?他感觉眼前的迷雾非但没有散去,反而更加浓重了。 当务之急,是找到赵德明留下的那个可能藏有翻案证据的铁匣子。赵铭是唯一的突破口。 然而,如何在不暴露自身的前提下,从一个对往事讳莫如深、且可能心怀怨怼的人口中套出线索,难度极大。直接询问铁匣子无异于自爆。必须创造一个“合理”的接触场景,并抛出足以打动赵铭的诱饵。 机会来自几天后的一次宫廷器物整理。内务府需清点一批库藏旧兵器,其中不乏前朝乃至本朝初年的军械,需要熟悉军旅之人协助辨认年代和制式。这差事自然落到了有军籍背景的赵铭头上。而御书房这边,因可能涉及某些御赐兵器的记录,需派人协同,李诚再次主动请缨。 在弥漫着灰尘和铁锈味的库房里,李诚终于有了近距离观察赵铭的机会。赵铭约莫四十岁年纪,面容憔悴,眼神浑浊,带着一种长期郁郁不得志的麻木,沉默寡言,只是机械地记录着兵器的特征。 李诚也不急,只是在一旁帮忙递送器物,偶尔根据弹幕提供的零星军事知识,搭一两句话: “赵书吏,这雁翎刀的弧度,似是前朝西北边军常用的款式?” “这枪头磨损痕迹,像是长期在沙地使用所致。” 他刻意将话题引向“西北”、“边军”,悄悄观察着赵铭的反应。赵铭起初只是嗯啊作答,但当李诚拿起一柄制式有些特别的短刃时,赵铭浑浊的眼睛似乎波动了一下,下意识地多看了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