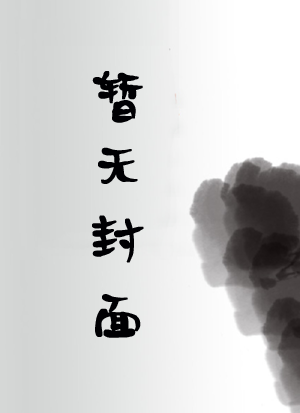第四章洞天福地天然居所
上天有好生之德。落海时赐予椅子,来到荒岛给予食物和甘泉,见我孤独送我奇犬,长夜漫漫,又送我石窝。冥冥之中,虽然从死亡之地昏暗懵懂而来,生的窗户开启阳光,现在阳光越来越温暖。
万物自然生长,我这个外来的异物要适应这个荒岛的,融入这里的沙滩、椰子、溪水、棕林、一叶一草,甚至阳光、雨露,成为它们的一员。
触摸狗狗的温暖的躯体,它正在安然入眠。它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碰到我这个新来的主人,喝着椰子汁,吃着椰肉和沙丁鱼,随遇而安了。看来,我也需要变成一条狗狗,活成一条狗狗。家乡虽美,掌柜虽好,亲人虽亲,而今却是天各一方。思念虽让我们抵近,但茫茫海水的现实使我们无法帮衬、感受到温暖,只有增添无尽的伤感。
今夜无需多想,无需细想,睡吧。
清晨,又是一个明亮的艳阳天。我与狗狗来到昨天最后一个水洼处,踩着溪流逆水而上。
开始,溪边的茅草和灌木很短,可以清晰的看见水流。走了百把步,植物变得非常稠密,完全遮挡了溪水。我用木棍沿着溪水往上翻,将植被向两边分,直到水流在阳光下显露清亮的容颜。
最初,担心植被下藏着什么毒虫水蛇之类,猛地蹿出来咬人,翻了一会儿,没什么异样,胆子大了起来,手脚也麻利,速度也快了。
其实我这种警觉实在是多余的,狗狗就在旁边,它的嗅觉听觉远远灵敏于我,有这个卫兵在一边,我只要听它的叫声就够了。人世间很多事情的道理都是这样的,明明是一点就透一想就明白的,偏偏要去经历一番担惊受怕一番,甚至要栽一个大跟头才吸取教训。究其深处,都是在意自己的判断,听不进别人的良言,看不见其他事物的长处。
额头的汗水与脚下的清凉在身体里中和,微风吹来,感到一阵阵的凉爽舒服。身后欢快的溪流,像小鸟唱着歌行走,忽隐忽明流向海边,又像一个蹒跚的孩子扑进母亲温暖的怀抱。
走了一千来步,前头,一个一人多高陡峭的山坡拦住了去路。双手抓住上头垂下的藤蔓,双脚蹬着山坡,爬了两尺来高,看到一处空旷的草坪,又退回来。双手把狗狗高高举起,放到草地上,又把木棍扬过头轻轻丢在上面。自己猛吸一口气,双手再次抓住藤曼,蹭蹭翻过山坡。
眼前的草地是长长的半月形,宽有四五丈,五六十丈,三面都是舒缓的山坡,从上面垂下绿色细密的藤蔓,藤曼很长,一直延伸到地上。草坪上稀稀疏疏长着两三尺高青色的藿香。面向大海,左边的山坡较高,从草地的近处开始依次上升,十来丈处大概就有两丈来高。右边的山坡较矮,前面只有七八尺高,快到月形的合拢处才与左边差不多一样高,两边连成一体。
左边山坡为青龙,右边山坡为白虎,又有活水,青龙宜静,白虎宜动,是天生建房居住的好地。在这个空旷的草坪,砍几棵大树,搭两间草屋,背靠大山,面望大海,足够遮风避雨了。
踏着溪流,用棍子敲打藤曼,撞击到硬物,拨开藤曼仔细端详,藤曼下面是墨绿的苔藓,划落苔藓,看到一块青色石头,与大地上石头并无二致。继续行走,敲击藤曼,回声一样,都是青石。
到了山坡一丈多高的处,看到一口房间大的水井,井边长着稠密的藿香,一路长到月形中间。水色清澈见底,有七八尺深,覆盖着一层稀疏的蓝色水草,水草下面是绿白相间晶莹的沙砾,水草里有细小的鱼虾悠闲的游动。捧起一口井水,水的味道甘美,有淡淡的红参的芳香。狗狗也学着我,先用脚爬了爬水,伸处舌头,喝起水来。
走近月形的中间,看到一处的藤曼左右的摇晃,拿棍子戳进去,里面竟然是空的。心中一惊,迅速往两旁拨弄,是一个一人多高的石洞。缓过神来,看见身边安详站立的狗狗,明白没有什么异样。
我蹲下身子,右手轻轻抚摸了两下狗狗的脖子,左手握棍指向洞里,告诉它我们准备进去。
猫着腰,双手持棍,小心翼翼的走进洞中,狗狗轻轻的跟在我右边。在洞里一会儿,光线虽然暗淡了一些,依然能看清楚东西,地面玉石一样蓝绿,沾满水得双脚感到有点湿滑,但是地面非常干燥。四周的石壁也是玉石一样的蓝绿,质感柔软,没有灰尘和蜘蛛网。洞很大,有三四间房屋那么大,有八九尺高,空荡荡的。空气没有郁闷的感觉,好像有清新的微风拂过。走到洞的中间,右边有个小洞,个把人高,于是向小洞走去。
站在小洞朝外看,有一个五六寸高的缝隙,可以看到外面的阳光,走近缝隙,仰着脖子往看,外面绿色的灌木青草,小洞与外面联通,风从这里进来。堵在小洞门口的石头颜色是黑黑的,用手摸了摸,有灰尘和泥沙。看来这些石头与石壁完成不同,大概是人堆砌的。从洞口反身,看清小洞里有一块墨绿的长石板,离地高约一尺,丈把长,占了小洞三分之二的长。
走到大洞,继续探索,在洞的底部,看到一行炭灰留下的汉字:十年离岛,落款是同治二年。这年离现在过去了整整五十年了。从洞底靠左边往外走,在小洞斜对面的有一块膝盖高的石板,长丈把,宽两丈,上面有一层黑乎乎的东西。我用木棍轻轻扫了扫,没什么动静,然后用手去摸,感觉是棕丝,那位前辈可能把这里当床。
过了石床,是一块空地,快到洞口的地方,有一张高约两尺长四尺宽三尺的石桌,桌上有个黑黑的长方形和两个拳头大的石头。捡起来看,长方形是一把锈迹斑斑的菜刀,七八两重,两个石头是取火的燧石,双手握住燧石一擦,冒出耀眼的火花。借助火光,看到下面是一张锅子,将锅子用手掂了掂,是一只铁锅。提起铁锅,底下是三块石头摆放的简易的灶膛,旁边有一堆茅草树枝。用棍子敲了敲没什么动静,再用手拨弄一番,茅草树枝很干燥,还能用。
拿起菜刀去割洞口的藤曼。刀口很钝,费了好大的劲才割开一人高三尺宽的口子,刚好够一个人进出。外面的光线透进来,可以清晰的看清十来丈的地方。洞口原来有七八尺宽,被严密的藤曼遮掩住,剩下的藤曼不再割了,姑且留住做门。
来到灶膛,提起铁锅放到一边。在柴草里找一些茅草和树叶,一点一点把灶膛厚厚实实的铺满。一手握紧一个燧石来回摩擦,火星不断掉落在灶膛里,摩擦了三五分钟,草叶里升起了青烟,又摩擦了一会儿,灶膛里出现来了火点。俯下身子,用嘴贴近草叶,轻轻吹了四五口气,扑哧一声,火光腾起。
点着了!赶忙找几根树枝,左右交叉参差搭在灶膛上,又往树枝上加上树叶和干草,火旺旺烧起。
老人讲人要实心,火要空心。如果不用树枝架起一个空间,再往灶膛加草叶,草叶会压下火光,火会慢慢熄灭。慢慢伸开两个手掌,往前去探火光,一会儿手掌感到很烫,收回来,慢慢往火塘加柴草。
烧了一刻钟的样子,感觉没有什么烟气熏染眼睛,于是加了几把大的柴草,还是没有什么烟气。烧了一会儿,火塘充满了火星,又加上一把大柴草,确定不会一下子熄灭,我走向洞外。
站在洞外看天,灶膛的上方冒着一排水雾般的青烟,慢慢向着天空消散。原来洞顶石头有曲转细密的缝隙,青烟大部分从这些缝隙飘向空中,洞里残留的烟子稀少,没有烟熏的感觉。将灶膛立在这里,与地理结合巧妙,曾经在这里居住的长辈应该经过多次的尝试,才把灶膛设在这里。
这个洞,有床有桌有灶,有锅有刀有火,外头有水有藿香,空气清新,地形开阔,是万里挑一的住房。收拾起来也简单,只需把石床打扫干净。
把石床上的东西全部搬到洞外,除了两套棕衣服外,全部是棕丝。棕丝已经很久远,挪到灶边当柴火。棕衣一套较重较厚,是冬天穿的,另一套较重较轻,是春夏秋穿的。用力扯了扯,很结实,还可以穿。
厚棕衣有个口袋,伸手进去摸,摸到一张泛黄的纸张,画了一张图,标了东南西北四个方位为,中间画了一个圈,写了一个岛字,纸的上方(北方)中间写了:北、岛,无人,空白处写120里;纸的下方(南方)写了:礁、空白处写120里,礁的正东方又写礁,标明150里,礁的南方标了一个岛,写着有船、10里。
图的下面有字:此洞可居,山腰有红参,水流春冬反。
看来这个圆圈是指这个岛,要从这岛到达那个有人的岛大概是280里,水的流向夏季和冬季是相反的。有人的岛极大可能是我乘坐的轮船经过的岛,现在是从东往西流,到了冬季应该是从西往东流。从第一礁石到现在这个岛母亲水流是从北向南,冬季应该是从南向北刚好相反。
我把图小心收起,把两套棕衣带到井边洗干净凉到草地上,自己也躺下了晒太阳。
正午的阳光有点热,身上奇痒无比,汗臭也扑鼻而来。仔细一看,衣服上满是污渍。在海水的侵泡下几日没有洗澡了,又不停走路,怪不得难受。
这样的太阳消受不起啊。爬起来,快步走到井边,三下五除二把衣服脱了个精光,扑通跳到井水里。憋住一口气,把头埋进水里,用双手使劲的搓头发,沙子、树叶、草尖等杂物从头发里搓出去。反复了多次,确定没有一点杂质。
让后洗脸、胸脯、腹部、大腿和脚趾头,全身感到前所未有的舒爽。跳上井边,双手把水滴抹去,让阳光把赤条条的身子晒干。地上的棕衣棕裤也干了,我穿上那套薄一点的棕衣。朝天,安然的躺下晒太阳。